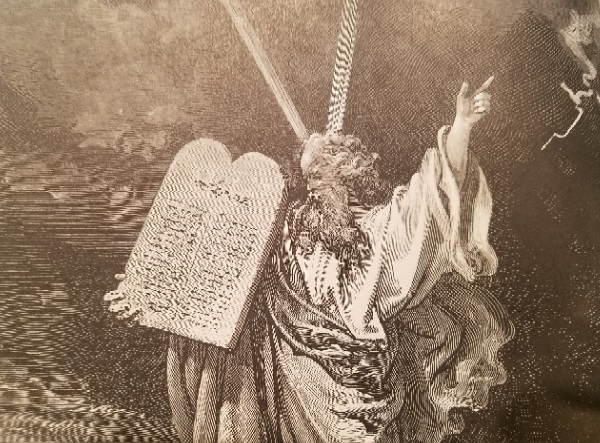
(續前)
第二章 預表論與信仰告白的詮釋
一、預表論(Typology)
解決[再版]問題的一個重要但間接的方法是考慮我們的信仰告白如何看待預表論,因為那些堅持行為之約在某種意義上再版的人,傾向於認為在摩西管治體系(Mosaic economy)中對預表論的理解更開闊而不是更局限。
毫無疑問,我們的認信標準確認了摩西管治體系的各項特徵,包括「應許、預言、獻祭、割禮、逾越節的羔羊以及其他預表和教儀」,都帶著預表的目的(WCF 7.5;見LC 34)。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認信標準幾乎沒有展開或闡釋摩西管治體系中的職分、人物、地點、事件、以色列群體或道德律的預表論,特別是當這些預表可能與基督有關時。認信標準對職分的預表論做了一些假設。當它們反思基督作為先知、祭司和君王時,也許它們是在暗示一些關於舊的約的人物(WCF 8.1;LC 42-45,SC 23-26)。在舊的約中,如果地點的預表論沒有得到確認,至少地點的象徵意義得到了間接而否定的確認,WCF 21.6告訴我們「在今天的福音時期」,一個人禱告的地點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此外,在解釋十誡的序言時,《大要理問答》似乎把預表意義歸給了出埃及記事件、以色列民族,或許還有埃及(LC 101)。儘管如此,對這些聖經神學的老生常談幾乎沒有任何實證的(positive)解釋。
更複雜的問題是 WCF 7.5 中提到的「其他預表和禮儀」究竟是指什麼。威斯敏斯特大會提供的佐證經文似乎有可能提供有關《信仰告白》和《大要理問答》作者所提到的「其他預表和禮儀」的一些線索。支持《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7.5 和《大要理問答》34 的原始經文不僅提到了割禮、無酵餅和逾越節的羔羊(羅四11;西二11-12;林前五7),也提到了過紅海是洗禮,磐石水泉是基督,以及亞伯拉罕和其他人對基督及其應許的前瞻性信心(林前十1-4;來十一13;約八56)。WCF 8.3 的引文進一步註解了亞伯和亞倫的預表意義(來五4-5、十二24)。我們應該在 WCF 8.6 中加入賦予女人、後裔和蛇的比生命更重要的意義(當然引用了創三15)。更重要的是,作為對 WCF 7.5 和 LC 34 的進一步支持,大會向讀者推薦了整個希伯來書八~十章,這些章節深刻地反映了聖殿、祭司職分和作為大祭司的基督。
然而,這些段落是否對其他預表和禮儀提出了任何具體主張?其實不然。宗教改革後的神學家們反思希伯來書的預表是很常見的事。但這些引文的範圍如此寬泛,並未表明任何特定的預表論立場或許諾。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再版範式以預表的方法(typically!)鼓勵對群體以色列(corporate Israel)、暫時的祝福和咒詛、以及對指向基督及其主動順服(active obedience)的道德律有一種具體的預表式理解(a particular typological understanding)。除了在 WCF 19.3 中將群體以色列稱為「未成年教會」之外,威斯敏斯特標準幾乎沒有提到這些主題。我們的認信標準既不肯定也不拒絕以一種預表論的進路來看待摩西管治體系中的道德律或《舊約》經文中的人物。作為對比,可能相關的是,該信條確實明確地將預表功能歸給了禮儀律,並將它們與恩典之約連在一起(WCF 19.3)。
但是,獻祭的命名法和大會為 WCF 7.5 提供的佐證經文是否可以合理地指出祭司工作是一種主動順服(有別於獻祭本身是一種被動順服 [passive obedience])?祭司順服的具體事例,以及以色列對這種順服的參與跟合作,是否可以提供摩西管治體系中積極行為原則的證據?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轉向了大會成員所製作的討論基督主動順服的文獻,但卻無功而返。關於主動順服或「完全順從(whole obedience)」的討論往往集中於捍衛基督主動順服的歸算,或集中於證明一個信徒主動順服他或她的主的持續義務:「基督的主動順服是我們所必須作到的一切聖潔和潔淨的榜樣與範式因[causa exemplaris]。」[42] 雖然祭司的工作總是被視為在預示基督,但在大會神學家的著作中,對祭司工作的討論似乎並未特別引起對基督主動順服的反思。這並不是說聖經沒有教導這個理念。儘管如此,無論是在對主動順服的反思還是在對祭司工作的反思中,大會成員似乎都沒有想到預示著基督主動順服的利未祭司順服的記載。[43] 進一步的研究可能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但從祭司工作的角度來看,提及「其他預表和禮儀……交付給猶太人」(WCF 7.5;LC 34)的用意,似乎不太可能是為了指出行為原則。
II. 觀點的多樣性(Varieties of Views)
也許尋找具體證據並不是最好的方法。約翰·費斯科(John Fesko)追隨布倫頓·費里(Brenton Ferry)的觀點,主張大會成員在撰寫《信仰告白》時,「只明確排除了關於行為之約與恩典之約的一種立場:『這樣看來,這並不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恩典之約,而是在不同時期下的一個相同的約』」,這是引用WCF 19.6 及其對托比亞斯·克里斯普(Tobias Crisp)教導之觀點的棄絕。這顯然是正確的。然而,如果這樣就得出結論說:「因此,《信仰告白》只排除了一種觀點」,大會雖然不認可「其他觀點」,但也「不排除」其他觀點,這是否言過其實呢?這是否會宣布一個比現有證據實際允許的更大的結論?雖然大會沒有採用如1675年的《瑞士公認信條》(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等狹義規定性文本(narrowly prescriptive texts)的模式,但大會的其他正面聲明很可能排除了再版的特定觀點。[44]
即使大會只明確拒絕對行為之約的實質再版的一種理解,我們認為本研究委員會有責任詢問,是否還有其他對再版的解釋,是與威斯敏斯特標準中所教導的教義相容、相衝突或相悖的。我們問到,是否可以證明,我們的信仰告白標準可能不允許某個版本的實質再版(substantial republication),但可能允許其他版本的實質再版。或者說,我們的標準是否承認墮落前與亞當所立的行為之約與摩西管治體系中建立的聖約安排之間存在印象上的平行關係(impressionistic parallel)?
我們認信標準中最引人注目的陳述之一,從摩西之約中行為之約的實質再版的角度來看,可以在《大要理問答》中找到,該問答在論及道德律時,說到:「人若遵行它……必得生;人若違背它……必要死」(LC 93)。冒著過度簡化聖經資料的風險,應許和威脅通常出現在盟約安排中,而赤裸裸的戒律通常是律法的特徵(但見 WCF 19.6)。威斯敏斯特大會將使用這種措詞來描述總結在十誡中的道德律,這可能表明其成員對於實質再版意義上的某種行為之約採取一種包容的態度。
沿著這些思路,威斯敏斯特大會最引人注目的決定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是它對律法的討論的基礎,甚至是其討論的依據,是決定引用支持WCF 7.2 描述摩西之約的經文,以解釋亞當的墮落前行為之約:加三12 和羅十5(引用利十八5),以及加三10(引用申廿七26)。[45] 如果大會的多數成員沒有看到墮落前的行為之約和摩西之約之間的實質連續性,大會怎麼會認為這些段落是相關的呢?
III. 信仰告白的詮釋
A. 佐證經文在信仰告白研究中的地位
誠然,使用特定佐證經文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信仰告白的議題本身。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威斯敏斯特神學家歸給這些經文的意義詮釋指南,這其中肯定包括那些認為這些經文與行為之約有關的人,以及那些認為這些經文提到律法或遵行律法(works of the law)的人,而這些律法或遵行律法是從行為之約中提取出來的;或從那些實際上斷言西奈山與加略山的稱義方式(means of justification)在救贖歷史上存在差異的人,到那些認為合法和非法稱義方式之間始終存在差異的人。對這些經文林林總總的詮釋將在本報告第五章至第八章中討論。
儘管如此,在《信仰告白》的這個地方使用這些經文引發了一個合理的詮釋問題。雖然這些引文本身並沒有為任何已知的實質再版範式提供支持,但神學家們想知道,如果可能的話,它們是否暗示了比行為之約在施行層面上的再版(administrative republication)更進一步的內容。畢竟,這些經文是信仰告白文本有用的詮釋工具。「在起草《信仰告白》的每個短語和章節後,大會進行辯論,然後批准了一系列支持該教義的經文。後來,議會要求該大會在發佈信仰告白的同時提供參考經文。大會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配合了,因為它沒有機會僅通過引用經文來解釋該經文的解釋。但是,一旦大會成員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們就會仔細選擇支持的經文,完善他們之前辯論中批准的經文清單。」在任何研究中嘗試「使用這些聖經經文來理解信仰告白的語句」都是值得努力的。雖然「《信仰告白》的現代版本有時會採用替代性的佐證經文,有時會為大會自己的教義提供更好的聖經支持」,但它們「無法洞察大會自己的想法」。[46]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本報告研究了歷史性的佐證經文。
B. 不是名稱,而是實體
在其辯論中,威斯敏斯特大會堅持認為它致力於考慮概念,而不僅僅是標籤:「我們詢問的不是名稱,而是實體(things)。」 [47]我們在閱讀有關該主題的歷史和最近的著作時,努力遵循這一規則,特別是在提及「行為之約」或「現世的祝福」(temporal blessings)的預表或教導目的(pedagogical purposes)時。[48]
閱讀早期現代文本時可能會出現其他警告。[49]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十七世紀的作家通常用對立的陳述來限定自己的立場,這種做法需要他們同時代的人以及我們在探討這些文本的幾個世紀時仔細聆聽閱讀。之後。威斯敏斯特大會上有一些神學家(實際上是他們一致的聲音),他們經常提供摩西之約與亞當的行為之約之間全面的平行對比,但隨後又用最清晰的措詞論證摩西之約在實質上是恩典之約。也就是說,某個大會成員可能堅持摩西之約是一個行為之約,然後在之後的某個段落(或某一頁)又堅持認為它只是在其施行形式上是行為之約。
例如,1647年,即《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文本定稿後的第二年,羅伯特·貝利(Robert Baillie)在一本反對浸信會實踐和釋經學的書中並列了有關摩西之約的陳述:
確實,恩典之約在基督以肉身降臨之前的施行過程中,披上了許多現在已被廢除的儀式的影子,並且在西奈山上與舊的行為之約相連,成為一位嚴厲的訓蒙師傅,為以色列難以管束的兒女,指出通往基督的道路,並透過威脅和咒詛使他們保持敬畏和恐懼;也透過它現世的諸多應許吸引他們順服:我們承認,由於這些附加物,恩典之約有時被稱為舊的約,並且與基督在道成肉身後所施行的恩典之約區分開來,西奈山的舊衣服被修改為一件舊外袍;但實體(the thing)始終是一樣的,深思熟慮的基督徒必定不願懷疑,因為如果主在律法以下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所立的約不是真正和實質上的新恩典之約,我們就想知道他們是透過什麼方式要麼獲得恩典,要麼獲得榮耀的;而且,誰敢如此放肆將舊的約的所有先祖置於如此殘酷的境地,將他們排除在恩典和榮耀之外?現在,如果我們承認,他們透過這個約在今生進入恩典狀態,並在來世進入榮耀狀態,我們又怎麼能否認它是滿有恩典的呢?
他們所說的一個混合之約並沒有多大意義,我們從未否認恩典之約在其首次施行期間,添加了許多禮儀和現世的應許以及整個行為之約;是的,在《新約》時期,施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的約不再需要所有的聖禮儀式和今生的應許;但這些附加物並沒有改變主體的狀態和本質;它永遠是一個純粹恩典的聖約,沒有任何混合;它既沒有在整體上,也沒有在任何實質部分上變成行為之約;如果它保持其本質,它就不會失去其名稱;它既不能完全被視為行為之約,也不能被視為恩典之約與行為之約的混合之約。[50]
讀者無疑會注意到以下內容。首先,貝利兩次或此或彼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說到,在恩典之約最初的實施過程(他指的是摩西管治體系,甚至整本《舊約》)中,行為之約是與之相連的(或譯為:是附加在其上的=adjointed to)。其次,這個注重行為的施行方式應許了現世的祝福。第三,他指出,禮儀和應許也是《新約》恩典之約施行方式的特徵,「其中的施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四,在一個重要的限定陳述中,他補充說,恩典之約的「地位」(state)或「本質」或「實質部分」,即使在摩西施行方式期間,「也不能將它完全視為行為之約,或恩典(之約)和行為(之約)的混合之約。」[51]
從這段文字和這些觀察中至少可以得出兩點。一方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將「行為之約」的標籤應用於摩西管治體系並不意味著作者認為摩西管治體系實質上是一種行為之約;他稱摩西管治體系為行為之約,但他認為這只是施行方式上的行為之約。他選擇將他的陳述並列在一起,而不是避免使用「行為之約」的語言。這種並置使貝利的表述成為正統的表述。它還需要廣角鏡頭才能拍攝全貌。簡短引用可能會產生誤導。
另一方面,詮釋者也會看到,貝利在摩西管治體系中看到了帶有教導目的的現世祝福(甚至詛咒);但他在《新約》中也看到了這些實體,對信徒和非信徒來說都是如此。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這一點在其他神學家的著作中甚至更加清楚,我們只需引用一處參考文獻就足夠了:托馬斯·古德溫(Thomas Goodwin)認為,「當基督統治時,我承認,祂很樂意在它們自己的範圍內,對這些合法的行為……給予獎賞」,例如「亞哈因謙卑而延壽」,或者古德溫從《新約》聖經中引用的例子。[52] 對古德溫來說,與現世的應許或詛咒相關的教導課程不僅適用於這個世界的亞哈,甚至「也適用於異教徒」。[53] 對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這裏我們的觀點很簡單,神學歷史學家不能透過引用這些神學家著作中的現世祝福來進行一項「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以仿造摩西管治體系所特有的一種實質上再版的行為原則。
這裏提到羅伯特·貝利的引言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從一開始就看到,將摩西管治體系描述為某種意義上的行為之約並沒有令十七世紀的牧師和神學家感到震驚,這對我們很有幫助。聖言的學生只是想知道「行為之約」這個標籤在摩西管治體系中的應用意味著什麼,然後他們才開始支持或反對一個人的特定觀點。我們讚揚這種在回應之前認真閱讀和傾聽的精神,特別是在涉及再版主題時。
C. 詮釋信仰告白的各段落
關於再版,我們的認信標準中最重要的一章可能是第十九章「上帝的律法」,其中的相關章節如下:
19:1 上帝賜一個律法給亞當,這是行為之約,上帝藉這約使亞當和他的後裔有義務個別、完全、切實、並永遠順服祂;人若遵守這約,上帝就應許他得生命;人若違反這約,上帝就警告他要死亡。上帝也賜給亞當權能與能力,使他遵行這律法。
19:2 這律法在亞當墮落之後,仍為義的完美準則,上帝就在西奈山以十誡的形式頒布這律法本身,且刻於兩塊石版上;前四誡是我們對上帝當盡的本分,其餘六誡是我們對人的本分。
19:3 這律法通常稱為道德律,除了這律法之外,上帝也樂意把禮儀律賜給尚未成年的教會,就是以色列民。其中包含象徵的禮儀:有些是關於敬拜,預表基督和祂的恩典、行為、苦難和益處;有些是說明各種道德義務的教導。今天到了新約時代,這些禮儀律都廢止了。
最近信仰告白詮釋者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涉及 WCF 19.2 中「(這律法)本身」(as such)的意思。「本身」一詞指的是「義的準則」(參19.2),或指被定義為「行為之約」(19.1)和「義的準則」(19.2)的「這律法」。事實上,提出這些可能性就是重申我們委員會正在審查的關鍵問題之一。
關於信仰告白與實質再版具有相容性的一些論點指出,第十九章的前兩段必須放在一起閱讀。章節中的段落編號不應讓我們分心,沒有注意到這一章是一個文學整體。如果把這兩段放在一起讀,至少有一種可能性,即大會允許或鼓勵有利於再版的解讀:「墮落之後」,摩西律法既是「行為之約」又是「義的準則」(WCF 19.1–2)。對這個論點最有意義的回應就是簡單地擴展它:因為當然第三段也必須在前兩段的背景下閱讀。如果把這三者結合起來看,就不會再把西奈山頒布的律法理解為某種形式的行為之約,而是一種生命準則。
更詳細的論證形式可以呈現如下。確實,WCF 19.2 中的「(這律法)本身」一詞要麼狹義地指「義的準則」(如19.2 中所述),要麼廣義地被定義為「行為之約」和「義的準則」的「這律法」(如 19.1 和 19.2 所述)。狹義的解讀可以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短語「(這律法)本身」可能更自然地修飾前面的短語(「義的完美準則」)。後者是更全面的閱讀,可以說它的優勢在於它以整體而不是以原子論(atomistic)的方式對待信仰告白的各段落。儘管如此,短語「這律法」在19.3 中再次使用,並且在後續討論中(如19.2 中所示,用近代詞表示延續),信仰告白澄清了所討論的「這律法」僅僅是「道德律」;大會在 19.1-3 中所考慮的是「通常稱為道德律」的律法。
勿庸置疑,如果否認第 19.3的「這律法」不是指前一段的律法,那麼對 19.2 中的「這律法」的使用也應適用同樣的推理過程(不管是什麼推理過程)。但這樣說就已經是多此一舉了,因為據我們所知,還沒有人提出過對19.1-3的這種解讀。值得注意的是,在 WCF 19章中有利於再版的討論中,並未留意到將這三段放在一起解讀的必要性。[54]
當然,我們確實想把這些段落放在一起來讀。在這裏,對某一章的段落進行連續且從屬的解讀不僅在語法上是必要的,而且在整個信仰告白中也是必要的。信仰告白各章的段落是為了一起閱讀而寫的。僅舉一例,正是由於對段落的不連續和獨立的處理,才導致這樣的說法,說WCF 3對假設的普世救贖(hypothetical universalism)持好感(或至少是包容);因為只有當該章的第 6 段和第 7 段相互獨立地閱讀時,信仰告白詮釋者才能得出這一在教義上和文本上都可疑的解讀。
假設的普世救贖的類比對於實質再版的討論具有一定的實用性。是的,這兩種教導之間存在不連續性:假設的普世救贖會腐蝕改革宗神學,而某些形式的實質再版則不會;假設的普世救贖涉及教義的微妙之處,這些微妙之處對於平信徒來說幾乎是難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有對實質再版的良好介紹,他們卻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假設的普世救贖的驅動動機是為了讓改革宗神學變得更溫和,而再版則希望增強它。但兩者之間也存在真正的連續性。在某種程度上,兩者都試圖解決解經的複雜性。威斯敏斯特大會的重要成員都持有這兩種觀點;而如果大會願意的話,這兩種觀點都可以更明顯地被排除在威斯敏斯特標準之外。也許最重要的是,雖然這兩種觀點都沒有受到熱烈的譴責,但它們都在威斯敏斯特大會提供的教義體系中找到一扇敞開的大門。
儘管如此,也許對 WCF 19.6 的更清晰的理解仍將使我們能夠在我們的認信標準中找到實質再版的位置。這段落開頭這樣說:「真信徒雖不在律法之下,稱義或定罪都不憑行為之約,但這律法對於他們或別人都大有用處……」實質再版的支持者同意,信徒因為處在恩典之約之下,所以不能憑行為之約而稱義或定罪,但他們認為,至少在《舊約》中,信徒可以出於個人稱義或定罪以外的目的而「處於律法之下」。
如果「行為(works)」一詞後面沒有逗號,那麼這種情況會更容易理解。此外,應該再次指出,信仰告白的文本似乎並沒有考慮到摩西管治體系,而且這裏引用的佐證經文也與舊的約的信徒的具體情況關係不大或毫無關係:羅六14;加二16,三13,四4-5;徒十三39;羅八1只關心救贖的施作,以及與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有關的益處。更重要的是,WCF 19.6 繼續斷言上帝的應許向基督徒展示了「上帝怎樣喜悅人順服,他們遵行律法會得何等祝福;不過律法對他們來說不是行為之約,他們沒有義務要遵守」。
這並不是要在此判定信條與實質再版或行為原則之間缺乏系統相容性(system-compatibility);而是說,它們之間缺乏系統友好關係(system-hospitability)。信仰告白的神學和釋經框架不一定反對實質再版,但也不是明顯的盟友。也許在我們的探究中,我們現在能說的最多的是,我們的信仰告白標準有時會調侃一些本身可能對實質再版友好的想法——但儘管如此,仍然與再版本身的任何真正關係相去甚遠。然而,如果我們要證實這個假設,就必須探討其他的信仰告白主題,尤其是關於創造、盟約、律法和功績(merit)的主題。
3 thoughts on “信正長老會(OPC)「再版」研究委員會報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