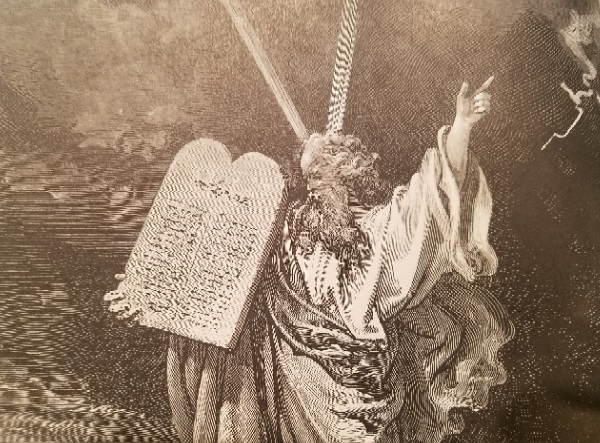
(續前)
第三章 律法與盟約
I. 創造與盟約
我們的認信標準中對墮落前盟約和摩西之約的處理在細節上並不是簡單明了的。認信標準反映了聖經,堅持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我們的始祖從一開始就明白什麼是「知識、仁義和聖潔」的真正本質。亞當和夏娃知道這一點,因為反映上帝性情的上帝律法「刻在他們的心中」(LC 17;WCF 4.2)。
雖是這樣,儘管我們的始祖擁有此形象,這律法也刻在他們心裏,但上帝與人類之間的距離如此之大,以至於除非上帝自願俯就我們,否則我們根本無法從祂那裏得到任何好處。上帝「自願俯就/降卑」的行動是為了立約(WCF 7.1)。換句話說,上帝的律法在創造時就栽種在我們心裏,但如果沒有盟約,我們就無法發旺,因此上帝透過「特別的護理之工」使我們的始祖與祂建立了盟約關係(SC 12)。[55] 這意味著,除其他外,創造似乎並不是立約的同義詞。
對某些人來說,聖約與創造的關係必須在這場辯論中起到主導作用。出於我們無法在此詳述的原因,一些神學家認為,只要承認盟約屬於護理範疇,就足以排除當前辯論中的某些立場。本委員會不相信情況確實如此,因為改革宗神學家對於盟約究竟是創造的一個方面,還是護理之工的一個方面,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問題上,即使是他們的「共同交戰者」(co-belligerents),也持有不同意見。因此,儘管存在相反的爭論,這個問題並不一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II. 律法與盟約
由此可見,道德律栽種在人類良心裏,與創造是同時發生的,然而造作一個盟約卻屬於護理的範疇。也就是說,從信仰告白的角度來看,他們心中的這律法並不是赤裸裸的;它(幾乎?)從一開始就披上了盟約安排的外衣。正因如此,在花園裏並非只有男人和女人孤靈靈地在一起。正是透過這種方式,他們才能夠與上帝同住,與祂建立關係。自然律似乎並不是行為之約的同義詞。
儘管如此,正如我們的認信標準所提出的,律法和盟約有許多共同點,尤其是它們都包含完美和個人順服的要求(參LC 93、99 和 WCF 7.2,19.1)。認信標準對盟約與律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精心細緻的闡述。
首先,信條對行為之約條件的描述只提出了完美的(perfect)順服、個人的(personal)順服的要素,而省略了永久(perpetual)順服的要素,這也許暗示著一個應許,即如果亞當和他的後裔通過了某種考驗期(probationary period),他或他們就會獲得一種加速的末世生命(WCF 7.2;譯按:即從地上的伊甸園,進入天上的伊甸園,享受永生)。相較之下,這律法,包括亞當在墮落前的地位下的律法,要求的是完美的、個人的和永久的順服(WCF 19.1 和 LC 93、99)。然而,儘管律法和盟約被表述為相似卻又不同,但信仰告白仍然可以說「上帝賜一個律法給亞當,這是行為之約」——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強有力的聲明,說明律法與盟約是同一回事(19.1)。[56]
其次,盟約似乎是比律法更大的範疇;盟約包含律法,因為律法本身似乎不像盟約那樣包括對罪惡和成功的警告和應許(WCF 19.1,尤其是19.6)。[57] 儘管如此,在 LC 93 對律法的描述中,要理問答指出該律法中包含警告和應許。律法具有盟約特徵,並且是在立約背景下提出的。或許要理問答文本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看到,律法確實以某種方式應許了一種普遍模式,即順服就得福,不順服就受損傷。或者,它可能將警告和應許視為每一種盟約施行的特徵,而不僅僅是行為之約的特徵。然而,正是在這一類的聲明中,主張對行為原則進行實質再版的人看到了向他們十七世紀的先祖,並進而向他們自己伸出的橄欖枝。
III. 歷史釋經
使這一說法更加複雜的是,現在回到上面提出的問題,威斯敏斯特大會投票決定提供描述摩西之約的聖經經文,以解釋亞當墮落前的行為之約的特徵。WCF 7.2 指出「上帝與人立的第一個約是行為之約」,並將其描述為「上帝在這約應許賜生命給亞當,並且在他裏面將這生命給他的後裔,條件是完全和個人的順服(perfect and personal obedience)」——為了支持這點,大會成員引用了羅馬書十章5節(引用利十八5),「人若遵行的,就必永遠活著」,以及加拉太書三章10節(引用申廿七26),「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詛。」勿庸贅言,這只會讓人更加好奇,即在為信仰告白提供這些佐證經文,以及在要理問答中提供這些經文的子集時,大會中的大多數人會看到摩西律法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如此充分地代表了墮落前的行為之約。[58]
關於大會腳註中這些聖經經文的出現,確切的問題是:大會成員和委員透過引用這些經文來支持他們在此提出的 WCF 7.2 中的聲明,其意圖是什麼?
上帝與人立的第一個約是行為之約(加三12),上帝在這約應許賜生命給亞當,並且在他裏面將這生命給他的後裔(羅十5;羅五12-20),條件是完全和個人的順服(創二17;加三10)。
如果大會指定的佐證經文是指向摩西管治體系中某種行為之約或行為原則的指針,那麼我們就必須證明,引用這些特定經文可能作為指向摩西管治體系所特有的行為原則之實質再版的指針。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確定在這個地方引用這些經文是否是為了傳達或允許一種行為原則,它不僅作為墮落前盟約的一部分,或作為生活在行為之約下的非信徒的持續準則,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對《舊約》信徒來說,也是摩西管治體系之本質的一個獨特(也許是預表論的)面向。畢竟,大會在為 WCF 7.2 的三個子句分別提供的佐證經文時,可能是為了表達更一般性或通用的觀點,而不是為了支持實質再版的觀點。
除了 WCF 19.1(以及 LC 92、93 和 SC 40)中這些相同經文所闡述的一般觀點之外,這些引文的一般目的對於 WCF 7.2 的三個子句中的每一個子句顯然都是合理的。例如,加拉太書三章12節本身引用了利未記十八章5節,它被引用來支持「上帝與人立的第一個約是行為之約」的觀點。加拉太書(以及利未記)的引用可以簡單地說明伊甸園中闡明的、並嵌入行為之約中的條件和標準繼續適用於人類歷史上所有的人。因此,大會澄清了這一點,因為它沒有引用明確提到墮落前管治體系的經文,而是《新約》時代引用的(加三12)摩西管治體系的經文(利十八5)——標記這樣一個事實的經文,即律法和生命的措詞表達了行為之約的條款。[59]
再一次,提到羅馬書的經文可能僅僅證實永生是作為行為之約的一個特徵而被應許的(羅十5,引用利十八5),並且該約的條款不僅與亞當有關,也與亞當之後所有的人有關(羅五12-20)。換句話說,它可能支持一個假設的、無法實現的行為原則,但這個原則在羅馬帝國時代和法老時代都一樣真實。
最後,引用創世記二章17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節可能只是為了支持盟約恆久的高標準:「以完美和永遠的順服為條件」(譯按:WCF原文應該是完美和個人的順服)。
由於這些文本的這些「一般解讀」是可能的,因此至少需要兩層論證才能在對羅馬書十章5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12節的引文中找到對實質再版的明確支持。少了這兩層論證,一切都無從談起。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我們必須找到正在討論這些經文的大會成員,而不僅僅是討論再版話題的成員。最近對十七世紀摩西管治體系中的行為原則的描述經常勾勒出早期現代神學家對再版主題所表達的各種觀點。另一方面,這項研究希望了解這些特定經文的詮釋範圍。當然,對再版主題的觀點調查是富有成效的,但它們對於解釋這些經文的引用並無用處。換句話說,僅僅證明大會成員在摩西管治體系中看到了某種行為原則是不夠的。一個滴水不漏的論證還必須找到與羅馬書十章5節或加拉太書三章10、12節的引文或引用相關聯的關於實質再版的討論,其中作者或演講者得出結論,說這些經文為以色列百姓獨有的行為之約或行為原則的實質再版提供了證據。
其次,我們必須檢驗這種假設,即一位大會成員引用利未記十八章5節或申命記廿七章26節(摩西管治體系的經文)並將其應用在墮落前的行為之約,將不可避免地具體談到了摩西管治體系。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毫無漏洞的案例,就必須證明這些經文被理解為與聖經中的以色列國信徒有關。可以說,引用利未記或申命記來描述墮落前的行為之約,可能並不能證明某位作者認為摩西管治體系本身就是信徒獨特的行為之約,也不能證明摩西管治體系獨有的行為原則就在眼前。例如,它只能證明上帝看到墮落前的管治體系和摩西管治體系之間的某些內容[material](而不是形式)連續點,或證明任何管治體系中的所有非信徒都處於行為之約之下。[60] 無論如何,很明顯,一些神學家在某種意義上引用這些經文來描述行為之約,但他們仍然將摩西管治體系視為恩典之約的一部分,並且必須理解他們立場的細微差別。[61] 只有當我們澄清了這些問題後,我們才能開始追問,作者是在何種意義上理解羅馬書十章5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12節的,以支持在摩西管治體系中再版的行為原則的想法(如果有的話)。
在閱讀這些經文的釋經評論時,我們發現了彼此互補與競爭的詮釋。此外,僅在道德律的討論(即與行為之約沒有明確聯繫的討論)中引用這些經文的情況並不罕見。為了說明各種詮釋的多樣性,我們可以考慮對加拉太書三章10節的處理。在大會成員中,這節經文經常被用來證明律法的標準是如此嚴格,以至於是在要求基督遵守我們所不能遵守的;[62] 道德律的要求是永遠不變的;[63] 如果我們想要得救,也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行為或我們應得的」;[64] 刑罰(或應許)是律法附帶的;[65] 很自然地,在亞當裏,我們應受律法的咒詛;[66] 而耶穌基督已經滿有恩典地為我們承受了咒詛。[67] 加拉太書三章10節通常只是為了闡明這些觀點而引用的眾多經文之一,並且經常與申命記廿七章26節、加拉太書三章12節和羅馬書第五章一併引用(但很少與利未記十八章5節一併引用)。威廉·高吉(William Gouge)認為加拉太書三章10節(以及加三12和羅十5)與這些引文的整體內容相反相悖,證明在「賜給亞當的……道德律」中有一種「律法上的義」,而這種義並不是新的約的「福音上的義」(evangelical righteousness)的特徵。[68]
上一段對加拉太書三章10節的解釋僅側重於道德律──詮釋各不相同。但擺在本委員會面前的問題不僅僅是律法,還有盟約。我們必須確定引用這段經文的人指的是摩西管治體系,更具體地說,是指摩西管治體系所特有的信徒的行為原則。畢竟,WCF 7.2 既談到了應許的生命,也談到了給予這種生命的條件。換句話說,信仰告白中的這一段不僅闡明了上帝律法的高標準以及違反律法將招致的懲罰,而且還闡明了上帝之約的應許,以及獲得其祝福的方法。同樣,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支持再版的學者想知道大會所引用的聖經文本是否暗示了摩西和墮落前管治體系所共有的某種行為原則。
衡量詮釋之合理性的最佳標準是考慮大會成員自己如何是使用這些經文的。這比釋經歷史學家所希望的要困難得多,部分原因是成員們在討論聖約問題的方式往往不太精確。對於聖約神學所採取的釋經立場和神學立場的多樣性十分巨大——比今天的多樣性要大得多,而在那些撰寫了關於聖約神學主題的完整專著的早期現代神學家中,這種多樣性要比那些把聖約神學作為各種定位中的一個定位來討論的系統神學家(如加爾文或杜仁田)中的多樣性大得多。相反,包括威斯敏斯特神學家在內的神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提到「行為之約」,彷彿它是一個可以與「道德律」互換的術語,而「恩典之約」,則彷彿是「福音」的同義詞。 [69] 因此,我們需要竭盡全力避免對歷史資料的錯誤引用,避免將施行方式的再版與行為之約的實質再版混為一談。為此,我們首先研究了這些經文的用法,只有當這些經文在大會文獻中與行為之約有某種明確聯繫時,我們才會使用這些經文;其次,我們試圖尋找證據,證明大會的釋經家使用這些經文是為了證實或支持實質再版或某種行為原則。
雖然不方便,但可以理解的是,我們很少看到所有這些經文像 WCF 7.2 那樣整齊地集中在一起。威廉·高吉將它們集中在一起,以論證利未記十八章5節、加拉太書三章12節和羅馬書十章5節正面表達了墮落前的行為之約的條件,而申命記廿七章26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節則反面表達了這些條件。[70] 更多時候,這些經文是單獨或成對討論的,而且往往是在保羅引用摩西五經的情況下。儘管如此,當我們在討論行為之約時,以這些聖經引文為著眼點來審視大會成員的著作時,還是可以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結論。特別是關於盟約(而不僅僅是道德律),對這些經文的通常解釋趨勢可以概括如下:
加拉太書三章12節(引用利十八5)
加拉太書三章12節經常在與聖約神學沒有明確關聯的情況下被引用,[71] 但若與聖約神學有關,經常會發現它與加拉太書三章10節一起出現,它被傳喚僅僅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證明存在一個強調順服的墮落前的行為之約。[72] 有時引用這段經文是為了強調墮落前的行為之約為亞當和夏娃提供了生命。[73]
羅馬書十章5節(引用利十八5);羅馬書五章12-20節
在保羅寫給羅馬人的信中的兩段經文中,最讓行為原則再版的支持者感興趣的是羅馬書十章5節。在大會成員的筆下,這段經文出現在聖約神學的討論中,是為了 (1) 強調在墮落前的行為之約中順服的必要性,此約在墮落之後,對所有非信徒來說都是永存的,[74] 或 (2) 僅在墮落前的行為之約中強調行為之約中生命的應許,或 (3) 假設性地將生命的應許擴展到所有時代的所有人,[75] 或 (2) 及(3) 。[76]
這些解讀通常允許摩西管治體系涉及實質再版——但只是作為包羅萬象的墮落後再版的一個方面,而不是作為摩西管治體系獨有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行為之約的再版只適用於非信徒,而不適用於信徒。也許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ong)是這一觀點最著名的闡述者。[77] 費里(Ferry)將它稱為行為之約「相對的、正式的」再版,正如他指出的那樣,《大要理問答》(LC 93)也闡述這種觀點的多種形式。[78] 值得注意的是,《大要理問答》引用了羅馬書十章5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12節作為證據。
再次,威廉·高吉(William Gouge),一個十分奇怪的人,他認為利未記十八章5節表明了一個對於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都適用的原則:「兩者都對人有要求」;一個要求順服,一個要求信心。[79] 高吉更常將利未記十八章5節與墮落前的行為之約和順服後得生命的應許連結起來。[80] 可以理解的是,他也將羅馬書十章5節視為在墮落前的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中提供了生命的應許。[81]
創世記二章17節;加拉太書三章10節
創世記和加拉太書兩段經文在大會成員的文獻中通常是成對出現的,其中一段或另一段最常被作為行為之約附帶著條件的證據,[82] 或作為這些條件是在咒詛那些在亞當裏但在基督之外的人的證據,或作為條件和詛咒威脅的證據。[83] 弗朗西斯·切內爾(Francis Cheynell)的結論具有大會解經家的特點,他認為加拉太書三章10節說明了伊甸園中的生命之約,「要求在咒詛的痛苦下完全和永久的順服。」[84]
關於摩西管治體系,大會成員都知道保羅在加拉太書三章10節和申命記廿七章26節的引述。儘管如此,與這些段落的連結一再強調「行為之約是正義的作為」[85],因此,在亞當裏,所有非信徒都受到行為之約咒詛的威脅。[86] 再一次,這些解讀允許摩西管治體系涉及大量的再版——但再版僅適用於非信徒,而不是摩西施行體系所獨有的。
雖然這裏並未列出所有常見解經思路的例子,而且還有我們沒有列出的其他排列,但在摩西管治體系中,沒有一個實質「再版」行為之約或行為原則的例子被故意遺漏。[87] 到目前為止,支持對這些經文作行為原則解讀的人寥寥無幾,這令你們指派的委員會感到驚訝和震驚,並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大會成員多麼接近於表達摩西管治體系中行為原則的某種實質再版,大會成員似乎沒有將該原則與這些經文明確聯繫起來。事實上,在討論與行為之約有關的內容時,大多數神學家似乎只是按照上面介紹的方式來理解這些經文。他們使用這些經文並不是為了論證摩西管治體系所獨有的預表論,以及因此也是教育性的行為原則(pedagogical works principle),而是為了表達所有不信的人都必須遵守的墮落前行為之約恆久不變的條件,包括對悖逆者的死亡威脅,以及對順從者的生命應許,雖然對於順從者來說,這或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生命應許。換句話說,大會成員在撰寫時並不會覺得這些經文暗示了舊的約的信徒的行為原則,或者暗示了與恩典之約中的繼承原則不同的國族以色列(national Israel)的繼承原則,也不會覺得這些經文支持透過行為而不是透過信心來獲得現世的祝福或避免現世的詛咒。
IV. 脈絡與系統(Strands and Systems)
即使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找到明確的證據,證明大多數威斯敏斯特神學家都將 WCF 7.2 中引用的經文理解為摩西管治體系獨有的行為原則,人們仍然要問,如何根據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問答中提供的主要思路來理解這些微妙之處。我們如何根據我們的信仰告白文本中的整體系統性的關注(overarching systematic concerns)來考慮這些思想脈絡(strands of thought)呢?畢竟,正如本章第一大段所論證的,在整個認信標準中,每一個墮落後聖約都從根本上被描述為一個恩典之約的一個方面或施行,一個具有不變實質的聖約,即使該施行方式有所不同(WCF 7.3 ;LC 33)。兩約內部和兩約之間的任何象徵性或救贖歷史對比,都只是對實質的、跨兩約的、不會改變的統一性的一層覆蓋層[an overlay](WCF 7.5, 7.6; LC 34)。
此外,為人預備的恩典之約的唯一條件是對基督的信心(LC 32)。如果這一切都是如此,那麼在基督時代之前和之後的恩典之約中,信心就是上帝子民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WCF19:6 的斷言是「真信徒雖不在律法之下,稱義或定罪都不憑行為之約」。對於理解再版的行為原則對於生活在摩西管治體系中的信徒的作用來說,必須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問答特別強調了這些斷言。這些並不是偶然的考慮,而是反覆的段落,在信仰告白中占了整整一個段落,而在大要理問答中佔了一系列問答。
相較之下,WCF 7.2 中的聖經引文所引發的思路似乎從未達到效果(never leave the station)。也許有一扇門被打開了,卻沒有任何內容進入信仰告白的其餘部分,以支持任何實質再版行為之約或行為原則的系統發展。在我們的認信標準中,這類原則從未被賦予任何預表論上的重要性。摩西管治體系在信仰告白中也沒有被排除在外(bracketed off),甚至在《舊約》中也沒有被賦予獨特的地位——事實上,整個《舊約》時期都被簡單地描述為「律法時期」(WCF 7.5)。[88]
在大會對律法的描述中納入威脅和應許的語言,然後引用有時被用來闡述行為原則的經文,兩者都是信仰告白中有趣的特徵;透過這些弱音而不是強音的引文,可能表達了一種意圖。或者,它們可能是大會辯論中引人入勝的人為產物(absorbing artifacts)。但似乎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這種意圖,尤其是在引用羅馬書十章5節和加拉太書三章10、12節時,因為沒有明顯的聖經含義或釋經傳統將這些經文與大會神學家期望他們的同時代人能夠認識到的行為原則連結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對這些資料給予最高的重視,也不能輕易地將其納入到我們目前的信仰告白框架中。因為我們必須把以盟約的實質與施行作為框架的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問答中包羅萬象的盟約內容,來對比這幾個不一致的特徵;事實上,考慮到我們的認信標準(而不僅僅是 WCF 19.1-3)提供的整體情況,「不一致」這個詞似乎是完全合理的。
(下一章)
照着经院主义的惯例,“matter”是不是应该翻译为“质料”?“material”是不是该翻译为“质料性的”?
Like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