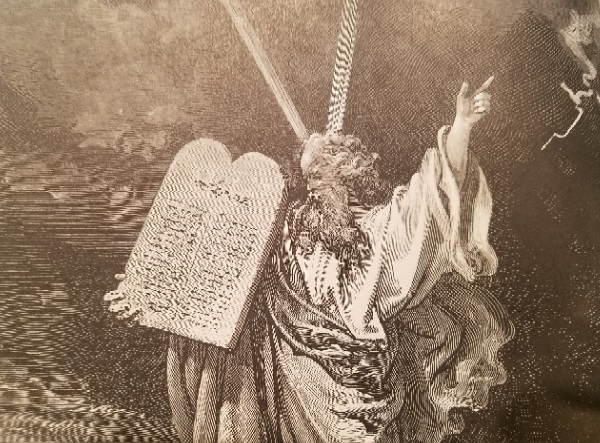
(續前)
第八章 克萊恩作為「施行再版」版本的倡導者
導言
獲得對克萊恩(M. G. Kline)的摩西之約神學更清楚的概念是本章的主要焦點。克萊恩對摩西之約中的「行為原則和預表國度[typal kingdom]」作出了複雜的闡述——如果簡單地闡述他的神學觀點,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微妙之處(nuances)。[196]
以下介紹的著作涵蓋了克萊恩出版生涯的各個階段,從他早期的作品《大君王條約》(Treaty of the Great King,1963年)到他最後出版的著作《上帝、天堂與哈米吉多頓》(God, Heaven and Har Magedon,2006年)。細讀克萊恩的全部著作,我們可以發現,他關於恩典之約的聖經神學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的改變。相反,從他最早的作品直到他的最後一部作品,出現了一種基本的連續性。
重點在於,雖然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本質上是恩典之約的兩種不同施行方式,但兩者都含有一個預表論特徵,即在其中包含了行為原則。最初在伊甸園起作用的行為原則把亞當的完美順服與末世產業(eschatological inheritance)連在一起。將具有代表性的順服與產業聯繫在一起的原則透過亞伯拉罕得到了救贖性的重新表述,並作了實質性的修正(參創廿二16-18;廿六5)。亞伯拉罕不完美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與預表產業的獲得緊密相關,這種方式既強化了以色列民順服的救贖特性(保存了預表產業),又為基督的完美順服(獲得末世產業)提供了一種預言性的預表(a prophetic type)。
如此,透過亞伯拉罕修改並根據罪與救贖的現實進行調整的行為原則,就進入了以色列國族層面的神治政體。以色列人的順從維持了預表國度,而以色列人的不順從則喪失了預表國度(參利廿六;申廿八)。當以色列沒有表現出亞伯拉罕的忠誠時,以色列作為上帝預表的兒子[typal son of God](出四23)就喪失了賜給順從的亞伯拉罕的土地產業。因此,以色列作為預表的兒子,透過放棄迦南暫定的(provisional)土地產業,大規模地重演了亞當的罪,並根據救贖歷史的預表特徵進行了調整。因此,原本將末世產業與無罪的順服關連在一起的行為原則,藉著亞伯拉罕在救贖歷史上得到了重新校準,使之適應於救贖預表論的關注,並以這種調整後的形式進入以色列國族層面的神治政體。對克萊恩的解讀,如果沒有將這一基本見解作為確定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national Israel)的行為原則本質的背景,就會導致對克萊恩思想中與預表論相關的救贖恩典缺乏認識。
儘管從早期著作到後期重要著作(如《天國序言》和《上帝、天堂與哈米吉多頓》),克萊恩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這一概念,但他對行為原則的這一構建在其思想中始終如一。至少有兩場爭論幫助克萊恩進一步明確了亞伯拉罕與國族以色列的獨特預表論功能,這兩場爭論分別涉及諾曼·雪佛(Norman Shepherd)的盟約神學和葛雷格·邦森(Greg Bahnsen)的神治國度倫理學(theonomic ethics)。相對於克萊恩,這兩位思想家的共同點是分別對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單調(flat)理解。例如,雪佛把亞伯拉罕的順從和接受祝福說成是在「救恩次序」(ordo salutis)層面上應驗了盟約,但他並沒有發展亞伯拉罕順從的預表論。[197] 同樣,邦森詳盡無遺地斷言摩西民事律的持久權威是社會政治倫理的不變準則,它約束所有執政者必須嚴格服從,但他並沒有展開神治政體內在的重要預表論特徵。[198] 克萊恩對亞伯拉罕和以色列預表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這些爭議的回應,因為他試圖澄清與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有關的救贖預表論的獨特特徵(unique features of redemptive typology)。
我們首先介紹克萊恩體系的一些主要輪廓,然後再詳細闡述這些輪廓。總體闡述將試圖從基本結構和重要限定條件(qualifications)的角度來捕捉克萊恩的思想,從而提供必要的微妙之處與精確性,以避免誤解和過度簡化,因為將克萊恩語料庫中的文本孤立起來,而不將其置於克萊恩本人提供的更廣闊的背景中,可能會產生誤解和過度簡化。儘管這一點還有待商榷,但對克萊恩的這一觀點將敦促我們,當我們花時間正確地解讀他時,他關於墮落後行為原則的概念並不能被實質再版的措詞所充分捕捉。克萊恩在魏司堅(Geerhardus Vos)開創的改革宗聖經神學運動的傳統內,對盟約神學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推進。
I. 原初論的闖入與預表論的闖入:伊甸園與迦南(Protological and Typological Intrusions: Eden and Canaan)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伊甸園代表著末世國度的原始歷史原型(original historical prototype),在其聖潔與(有幔子遮蔽的)榮耀中,闖入(intrude)到今世;而以色列的神治政體則代表了同一個未來國度的第二次預表性的闖入(typological intrusion),這次乃是按照罪和救贖的現實作出調整後的形式闖入的。未來神治國度的聖潔以原初形式[protological form](伊甸園)和預表形式(迦南)的投射或闖入,構成了克萊恩盟約神學概念的核心結構。(譯按:protology原初論,與eschatology末世論相對,前者指起初的事,後者指末後的事,兩者共同描述了上帝救贖歷史的發展。)
伊甸園作為聖潔神治國度的創造,「如果從完滿成全國度預期實現的角度來看,就是一種末世論性質的闖入(eschatological intrusion)。如果從已經存在於天上的上帝聖所領域向下投射的角度來看的話,這就是宇宙論性質的(具體而言,是天國的)闖入(cosmological intrusion)。」。[199] 伊甸園是原始的、原初的(protological)神治國度領域,它以臨時的形式體現了末世國度的神聖性。換句話說,「造物主在伊甸園中預備了自己天上居所的一個地上複製品,這個地上的居所要作為一處聖所,人類可以在其中履行自己的祭司職份。」。[200] 他詳細闡述道:
伊甸園被選為榮耀-聖靈擺放寶座的核心場所,是宇宙聖殿在地上的微觀模型,也是天上聖殿在地上可見的局部投影。起初,人類原本的住所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這個位於伊甸園的核心聖所原本是要成為一個媒介,藉此人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驗到上帝同在的喜樂,並且在這個歷史旅程的最初階段裏,在最契合人類作為地上受造物的本性與狀況的尺度上,與上帝同行。[201]
用表達對亞當和他所代表之人的關切的措詞來說,「伊甸園中的國度是以馬內利的國土,是榮耀-聖靈臨在的聖所,是神治國度的樂園—保護國(protectorate),其中作祭司的聖潔國民住在與造物主的聖約團契中。」[202]
為了將原初的闖入與亞當作為祭司-君王的身份連在一起,伊甸園是原始的、被[末世國度]闖入的國度領域,上帝交付亞當的任務是藉著完美的、個人的、確切的和完全的順服將伊甸園歸耶和華為聖,使這園子成為聖潔。亞當的順服至少與伊甸園的兩個特徵有關。首先,為了保護伊甸園不受玷污,亞當必須持續不斷地順服。其次,當亞當接受考驗時,他的持續順服是超越伊甸園的試驗期、進入安息日安息的指定方式。亞當旅程的「第一階段」包括以祭司的身份向耶和華獻祭,以及在耶和華的統治下與古蛇鬥爭。如果亞當在行為之約下保持順從,與上帝的關係將得到晉升。這就是伊甸園處境下的末世論。
但要理解克萊恩關於伊甸園中行為之約的概念,關鍵在於:一個聖潔國度和一群聖潔子民與亞當完美的、具有代表性的順從是相輔相成的。亞當作為盟約元首的完美順服是亞當和他所代表之人超越試驗期進入安息日安息的途徑。亞當的順服與末世國度的產業是緊密連在一起的,這種關連提供了一種關鍵的神學建構,幫助克萊恩闡明,其他人的順服如何獨特地與獲得(亞伯拉罕)或維持(國族以色列)預表的迦南土地產業連在一起。
因此,就亞當作為行為之約下的盟約元首而言,與造物主君王的相交關係旨在透過亞當藉著受過試驗的順服而超越其試驗期的地位。正如克萊恩所指出的,「創造之約的祝福條款提供了完滿成全國度的賞賜,而行為原則——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則支配著人類是否能獲得這一獎賞」。[203] 他說道:「根據造物主規定的條款,必須在人類忠實地完成試驗期的行為的基礎上,他才有權進入安息日的安息。」。[204] 有鑒於此,克萊恩繼續說道:「那麼就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聖約神學將這種試驗安排視為一種行為之約,因此使它與恩典之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5] 從無罪(innocency)晉升到榮耀的途徑(參WCF 9、2、5),是亞當作為其子孫的盟約元首,按照行為之約所作的完美、個人、準確和完全的順服。
透過完全順服,從無罪走向榮耀的過程,與救贖恩典的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應許藉著對基督的信心獲得救贖;末世論先於救贖論(eschatology precedes soteriology)。也就是說,在行為之約中,離開基督的救贖中介,末世的榮耀是可以實現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亞當的順從具有立約的性質,克萊恩談到了一種「恩典」,這種恩典為那「出於塵土無權聲索的受造物」(the claimless creature of the dust)[206] 提供了完美順從的末世生命,儘管這種恩典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具救贖性,也沒有把信靠基督納入視野。然而,與此同時,亞當作為一個無權聲索的受造物,也可以從上帝自由的良善中「賺得」(merit)末世的生命。(譯按:這是上帝自願俯就所賜下的白白的恩典,藉著行為之約,亞當可以藉著完美的順服得著末世生命,但這種順服本身毫無功績可言,亞當作完了一切順服,只是無用的僕人,並不能賺得永生;他之所以能得到永生,完全是出於上帝在約中白白的應許,聖約神學家稱之為「盟約功績[ex pacto merit]」)。
克萊恩澄清說,重要的是要記住「恩典存在於救贖前的盟約中。因為上帝為人類提供了最初福祉的完滿成全,或者更確切地說,上帝從一開始就為人類加冕的全部榮耀與尊貴,是上帝向這個出於塵土無權聲索的受造物展示了恩典與良善」。[207] 然而,從這一自願俯就的仁慈行為中,克萊恩提出了以下斷言:
上帝是公正的,並且祂的公正體現在祂所有的作為上,尤其體現在祂所設立的盟約之中。創造之約的條款——完成規定的服事後就得到規定的獎賞——正好揭示了這種公正。作為對上帝公正性的啟示,創造之約的條款定義了公正的含義。根據這個定義,亞當因著順服會賺得永恆生命的獎賞,其中並不涉及到一絲一毫的恩典。[208]
在這兩段陳述中,克萊恩一方面區分了作為恩典與自由之表達的末世晉升的邀約(the offer of eschatological advancement),另一方面區分了末世晉升的實際條款,後者要求出於盟約的公正(ex pacto justice)獎賞完美的順服。對「出於塵土無權聲索的受造物」提供末世晉升的最初邀約展現了上帝的(非救贖性的)恩典與良善,而透過完美順服來獲得晉升則引發了上帝出於盟約的公正。
從這一背景出發,克萊恩還將以色列在迦南的神治國度理解為對末世國度之聖潔的預表-救贖闖入(typico-redemptive intrusion)。他說到:「在摩西時期建立的神治國度,是伊甸樂園-聖所的救贖性更新(redemptive renewal),並且是完滿成全的永恆神治國度聖所的原型預覽(prototypal preview)。」[209] 換句話說,克萊恩進一步指出:「只有透過救贖性的闖入(redemptive intrusion),以神的顯現為中心的聖地才會重新出現在原本並不聖潔的、墮落後的世界裏——這在以色列預表性的神治國度的崇拜中最為突出」。[210] 有鑒於此,他指出:
與此相稱的是,與在舊的約之下象徵性的國度的闖入相關的,還有在有形領域中存在著末世復興權能的闖入,例如將最終的救贖審判原則預先應用在以色列人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征服迦南,另外還有從巴比倫被擄歸回家園,儘管這種權能也貫穿了摩西律法的統治-司法規定。[211]
因此,除了來世的聖潔闖入到墮落前、原初的國度中之外,還有末世國度的聖潔,以預表論的方式第二次闖入到以色列神治國度中,而這第二次闖入具有救贖的特性。正是在這些截然不同的闖入事例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對克萊恩思想中行為原則的原初事例(protological instance)和預表事例(typological instance)作出區分。伊甸園中的原初闖入實質上並不具有救贖性,而迦南的預表闖入在實質上則具有救贖性。這一區分支撐著克萊恩關於原初論形式和預表論形式的行為原則的神學,並解釋了行為原則分別應用於亞當和以色列時出現的實質差異和形式上的相似性。
II. 原初論、預表論和行為原則(Protology, Typology and the Works Principle)
迦南的救贖性闖入與伊甸園的救贖前闖入有何關連?在伊甸園的原初闖入和迦南地的預表闖入之間出現了實質的不連續性。克萊恩提出了把握亞當在伊甸園的順服與以色列在迦南的順服之間的區別與關係的一把鑰匙,他說:「在摩西管治體系中,整體上再現了創世時的秩序(然而受到了人類墮落境況的限制,並伴隨救贖進程而產生的調整),尤其是涉及到了起初的伊甸園秩序的本質,它既是神聖的樂園—神國,也是對人類行為進行試驗的一種安排(a probationary-works arrangement),這一點對我們當前的論點尤其重要。」。[212]
這裏所說的「限制」和「調整」至少包含以下區別:一方面是亞當作為上帝的兒子在伊甸園神治國度領域的順服,另一方面是以色列作為上帝的兒子在迦南神治國度領域的國族順服。他透過以下方式發展出這種區分:
完美無瑕的順服是亞當繼續留在伊甸園的條件;但以色列在迦南的居留權則取決於維持某種程度的宗教忠誠,這種忠誠不需要是對所有以色列人的全面忠誠,也不需要是對那些真以色列人的完美忠誠。上帝行使或限制審判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源於祂統治以色列的主權恩典基本原則。儘管如此,上帝的審判還是維護了以色列歷史中預表-象徵信息的利益。[213]
克萊恩在這裏提出的幾個觀點值得仔細研究。一方面,亞當的順服被理解為「完美無瑕」的順服,這種順服與他的地位——無罪的地位——相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亞當必須做出完美的、個人的、準確的和完全的順服,才能超越試驗期,進入安息日的安息。透過他代表性的、完美無瑕的順服,上帝將把榮耀國度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要獻上「某種程度的宗教忠誠」,這種忠誠不一定要「全面」涵蓋所有以色列人,也不一定要在真以色列——選民中做到完美無瑕。以色列的順從同樣表達了一種地位,但在以色列的情況下,它是恩典的地位。因此,亞當在伊甸園的居留權與以色列在迦南的居留權之間的根本差異,就在於無罪之人的「完美無瑕」的順從與得贖的立約子民所表達的「某種程度的宗教忠誠」之間的區別。
這種區別體現了無罪的盟約元首的順服與得贖的立約子民的順服之間的根本差異。宗教忠誠的前提是救贖的關係。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要表達出對耶和華的宗教忠誠,耶和華將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救贖的榮耀伴隨他們從埃及到曠野、再到迦南。在克萊恩看來,宗教忠誠是一個短語,它喚起了「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參申六7,該節從出埃及的角度這樣說)」這一核心救贖現實。以色列與亞當不同,是在救贖、盟約安排下用寶血贖回的子民。因此,對宗教的忠誠並不是毫無瑕疵的順從,而是那些被恩典用寶血從罪惡和奴役中贖回的人的不完美順從。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9.2、4)中的措詞來表述克萊恩的觀點:亞當作為無罪的盟約元首,是在無罪的狀態下順服;以色列作為得贖的子民,是在恩典的狀態下順服。這一區別明確地解釋了因著罪和救贖過程而引入的限制和調整。
但是,克萊恩的評論還提出了另一個關鍵的不連續性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上帝為什麼沒有像對待墮落的亞當那樣立即對以色列人的罪孽施行審判的理由。克萊恩指出:「上帝在行使或限制審判時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源於祂統治以色列時的主權恩典基本原則。」對亞當悖逆的審判幾乎是立即執行的,但對國族以色列的審判卻有一段相當長的延遲期。這要怎麼解釋呢?
對以色列審判的延遲,其原因在於主權恩典的基本原則。並不是普遍恩典暫停了審判,因為普遍恩典正是在神治國度中被暫停的;相反,是主權恩典的基本原則解釋了對以色列的審判為何被擱置。由於存在著在恩典之約的框架內以主權方式施行的潛在的、救贖性的恩典,以色列不會因為罪孽立即受到審判。正是這項基本原則解釋了對亞當所犯罪行的即時審判,以及對以色列數百年來無數罪行的長期法定程序之間的不連續性。
然而,克萊恩同時指出:「儘管如此,上帝還是如此施行祂的審判,以至於以色列歷史的預表-象徵信息的利益得以保存」。儘管上帝根據主權恩典原則耐心地對待祂的子民,但祂還是根據以色列歷史的預表-象徵信息審判了以色列。這個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並沒有向上帝獻上適當的宗教忠誠,他們變得像周圍的民族一樣,從盟約歷史來看,像亞當一樣犯罪、被擄,並失去產業。
以色列的預表-象徵信息是,儘管以色列蒙恩得贖,並被賜予迦南地的產業,但以色列人卻摒棄預表的事實陳述(typical indicative)——上帝在恩典之約中的恩典供應——並熱衷於長期的背道,不忠於上帝,悖逆上帝。因此,上帝審判以色列人的方式與割禮的聖禮-記號的雙重賞罰功能一致——不信者要被剪除。克萊恩認為,割禮這個記號本身就描繪了上帝的審判,如果守約,審判就會降臨在即將到來的中保身上;如果背約,審判就會降臨在背約者身上。以色列人透過割禮象徵性地承受了上帝所威脅要降下的忿怒和詛咒。[214]
克萊恩將國族以色列的順服與土地的保留或喪失相對應,正是這種預表論功能被稱為「行為原則」。克萊恩在其晚期著作《天國序言》中闡述並擴展了這一原則,他認為,
利未記十八章5節藉著指出履行聖約規定的人就必活在這些規定中,宣告說,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必須遵行律法的要求,才能享受預表國度群體的祝福。即使就永恆救贖這方面來說是選民的個體,也會因為各種嚴重違反律法的行為,而從那個暫時的、預表的領域中被剪除,來作為懲罰。同樣地,只要以色列國民向他們天上的君王維持適當程度的忠誠,他們就可以集體地在應許之地維持自己的神治國度。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會失去預表國度,就會在那個集體的、預表的意義上失去作為上帝百姓的特殊身份。如果他們違背了聖約,就會遭到被擄,在預表的層面上失去蒙揀選的國家身份。[215]
克萊恩在此表達的是前述論點的延伸。他認為,「適當程度的民族忠誠」就可以維持在迦南地的居留權。如果不能表現出這種適當的忠誠,就會失去預表的土地產業。因此,行為原則與居住在被闖入的迦南聖地的全體以色列民之獨特的、預表的象徵意義密不可分。因此,克萊恩試圖透過行為原則的措詞來捕捉在民族層面表達對上主忠誠的意義,相對於預表性的迦南聖地。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的順從/不順從與預表的迦南產業-土地的保持/喪失密不可分。
因此,與亞當的連續點,並不在於要求「完美無瑕」的順服,以超越試驗期;相反,這種連續點在於順服乃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與被闖入的神聖領域(就亞當而言是原初的神聖領域,就以色列而言是預表的神聖領域)有關連。亞當完美無瑕的順從將使他和他的子孫從原初國度領域進入末世國度領域。以色列的「民族忠誠」將使以色列能長久留在預表的神治國度產業迦南地,而不忠則會喪失同樣的權利。因此,預表性的行為原則要求在原初之子[protological son](亞當)和預表之子[typological son](國族以色列)的順從之間建立關聯(經過適當的救贖調整)。在上帝的救贖-歷史教導中,以色列作為上帝兒子的神治國度身份旨在複製亞當作為上帝兒子的罪惡和放逐。克萊恩思想的重點在於每個兒子不順服的結果,特別是與被闖入的神治國度神聖領域的關係,該領域以臨時和預期的形式體現了來世國度的榮耀。
克萊恩在《天國序言》中闡述如下:
這個行為原則在申命記中有詳盡的闡述,就是後來在以色列人剛要進入迦南地之前、重申西奈之約所作的條約記錄。就在聖約重申儀式的高潮時刻,百姓被提醒耶和華對他們的要求,並被呼召在善與惡、生命與死亡之間做出選擇,之後他們再次肯定了要效忠於神聖的耶和華(申廿九章)。然而,以色列人轉而繼續違背他們所起的盟約誓言,世世代代屢次悖逆,在申命記後面的《舊約》經書,正是記錄了在士師與列王時代、以色列人不忠於耶和華從而演繹的血淚史的資料。此外它們也講述了,申命記式條約中威脅人不要悖逆的咒詛,是如何襲擊這令人厭惡的國民,直到上帝將以色列人趕出神聖的樂土,使他們被擄到東方,這就是他們受到的最終懲罰。從迦南之地被驅逐出來,恰似一段曠日持久的法定程序的最終結果,這個法定程序正是由上帝提出來控訴以色列人的,是藉著祂的僕人眾先知進行的一場盟約訴訟。儘管以色列人一遍又一遍受到警告,但是他們仍然蔑視先知的教訓,直到上帝將他們從聖所與蒙福之地剪除為止。對古代國際條約施行的記載,證實了這種相同的法定程序,其中大君主會委派特殊的使者作代理,對悖逆的附庸提出訴訟。
當我們轉向在創世時所立之約的歷史結局時,我們會發現那段歷史與西奈之約的情況何其相似。創世記第三章也是一段關於違背聖約的悲慘記錄,後面緊隨著上帝的訴訟以及對咒詛的執行,就是將人類從神的聖所–樂園趕了出去,使他們在伊甸的東邊過著流放的生涯。[216]
請注意這裏的關鍵措詞:「行為原則」與「曠日持久的法定程序」是一致的,透過這一程序,以色列人「一遍又一遍」受到警告要對耶和華表達適當的忠誠。大規模的持續背道最終導致以被擄的形式實施詛咒。最重要的是,克萊恩強調以色列人只要向耶和華獻上適當的忠誠(利十八5),就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繼續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以色列人長期背道,表現為持續拒絕耶和華的盟約恩典,最終導致被擄,我們正是從以色列人長期背道的過程中,發現了與「創世記第三章」的關聯,以及類似的「違背聖約的悲慘記錄,後面緊隨著上帝的訴訟以及對咒詛的執行,就是將人類從神的聖所-樂園趕了出去,使他們在伊甸的東邊過著流放的生涯」。
克萊恩將以色列人與亞當進行比較時,並不是將創世記第二章中墮落前的亞當與末世產業對完美無瑕的順從的要求連在一起。相反,當克萊恩將以色列和亞當拿來作比較時,我們看到的是創世記第三章中墮落後的亞當與他因犯罪而被逐出伊甸園以東的後果之間的關聯。克萊恩並不是從與墮落前的亞當重新訂立行為之約的角度來考慮的(in terms of a republication of the covenant of works with pre-fall Adam),而是讓我們看到墮落後的亞當與產業的喪失是一種以救贖為條件的行為之約的重演(a redemptively qualified recapitulation)。從行為原則的角度看以色列與亞當的關聯,這是需要把握的一點。因此,在迦南預表國度的救贖闖入中,克萊恩發現了適用於國族以色列的行為原則的存在,並以適應罪、恩典和救贖預表論現實的形式重演了亞當的罪和被擄。
III. 與行為原則有關的預表「功績」: 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國族以色列順服的救贖–歷史原型 [217]。
到此為止,克萊恩對恩典和救贖預表論的強調似乎已經足夠清楚了,但我們還需要理解並分析他的「功績」概念,因為它與國族以色列在一種受行為原則支配的安排中的順服有關。
為了提前總結論點,理解克萊恩的預表功績(typological merit)概念的關鍵在於亞伯拉罕的順服所扮演的獨特角色。從一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尋常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是基督有功績的順服的預言與預表記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服是歷史原型(historical prototype),它規範了以色列人相對於維持預表國度產業「有功績的」順服的本質。亞伯拉罕的順從具有獨特的預表功能,它既預示了基督,也為國族以色列所提供的那種類型的順從提供了原型。
克萊恩指出:「亞伯拉罕是第二個亞當的原型,是新人類的族長,在他身上,國度-家族的伊甸理想得到了實現,而這一理想最初是在亞當面前設定的。」 [218] 也就是說,正如全人類都會因原初亞當(protological Adam)完美的個人順從而蒙福那樣,亞伯拉罕的情況也是如此。亞伯拉罕是一群新人類之父——一個救贖性的盟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上帝的末世目的正透過對所應許的彌賽亞後裔的信心而得以實現。
更具體地說,克萊恩指出了改革宗解經家必須解決的一個具體問題:「亞伯拉罕的順從如何與舊的約形式的國度祝福的保障連在一起,這是人類行為在救贖性的盟約中的作用這一廣泛主題中的一個特殊問題。」[219] 克萊恩的觀點是,正如上帝會在非救贖性、滿有恩典的俯就的大背景下(見上文),根據功績的盟約原則(ex pacto principle of merit)來獎賞亞當那樣,亞伯拉罕作為新的得贖人類的預表元首,也有類似的情況。亞伯拉罕的順服完全是在救贖的背景下進行的,與伊甸園中的亞當相似,但考慮到罪、救贖和救贖預表論的現實,會有明顯的「限制」和「調整」。
克萊恩補充說,亞伯拉罕的順從不僅得到了獎賞,還表明了亞伯拉罕的順從與彌賽亞應許給他及其後裔的預表國度之間的獨特關係:「然而,當我們把這個問題追溯到上帝向眾族長所作的立約啟示時,我們就會遇到把賞賜國度的應許,與亞伯拉罕對耶和華所作的忠心服事聯繫起來的一些陳述。」。[220] 克萊恩擴展了他的觀察,認為,
創世記十五章1節的景象是要表達,這位偉大的君王表彰亞伯拉罕遵守了聖約義務的顯著表現,因此要給他特別的賞賜,這賞賜會遠超過亞伯拉罕因忠於耶和華,他自己的主的緣故,在所多瑪王手中所放棄的任何財富。耶和華與亞伯拉罕交往的更廣泛的記錄,包含了許多與古代君王賞賜忠僕的措辭相平行對應的關鍵語,這樣的僕人是順從命令、無可挑剔地獻上服事,並且行在主人面前的人。[221]。
他接著說到,
亞伯拉罕另一次傑出的順從盟約的表現,也是所有的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帝第二次啟示的時機,將亞伯拉罕之約的祝福作為對這位僕人順服行為的賞賜。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上獻祭的最後一刻,耶和華的使者,也就是最終要成為上帝唯一的兒子和替代性的羔羊祭物的那一位,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廿二16-18)[222]。
克萊恩進一步澄清了亞伯拉罕順服的本質與功能,他區分了亞伯拉罕所作的、由聖靈造作的、出於信心的順服(救恩次序中常見的順服)和這種順服的獨特預表特性(救恩歷史中獨有的順服)。他認為:「雅各從信基督因而被稱義的角度來審視這件事,將亞伯拉罕的順服解釋為證明他有信心的關鍵行為(雅二21及後面經文)。但是這件事既要從個人主觀經歷救贖的角度來看,也要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理解。」[223] 儘管亞伯拉罕的順服展示了聖靈造作的信心,這種信心使信徒與彌賽亞聯合,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但從救贖-歷史的視角來看,同樣的順服則表現出獨特的預表性。換句話說,亞伯拉罕是所有信徒之父,因為他和信徒都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行事,但他因信而順服也對後來的救贖歷史進程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是一種獨特的、不可重複的預表功能。
克萊恩進一步解釋道:
亞伯拉罕的順服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是上帝將來恩待他後裔的基礎,這一點由耶和華之後多次向以撒重複這個神諭的實質內容,得到了證實(創廿六2及以下)。在重申了一定會履行給以撒及其後裔的聖約應許的承諾後,耶和華最後總結道:「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創廿六5,參第24節)。在這裏,亞伯拉罕的行為的意義,就不能僅限於起到了確證他的信心的作用。亞伯拉罕忠心地履行聖約的義務,在這裏被清楚宣告為是以撒和以色列人蒙福的原因。他的行為具有使他人享受獎賞之有功績的性質。[224]。
克萊恩進一步闡述了亞伯拉罕的預表意義,他的論述如下:
由於亞伯拉罕的順服,救贖歷史會以亞伯拉罕的後裔組成神國的形式呈現出來,救贖祝福由此興起並且流向萬邦。上帝樂於用亞伯拉罕的模範行為作為獎賞的基礎,將那要被塑造成預表國度(也就是孕育基督的母體)的獨特角色,賜給按著肉體來說的以色列人。在這個預表結構之中,亞伯拉罕出現了,他要成為他那憑應許而生的彌賽亞後裔,即耶和華僕人的一個約定的記號,後者履行自己的聖約使命,構成了在萬國中揀選出來的真以色列人得獎賞的基礎,他們要承受預表所對應的那個末世性國度。當然,亞伯拉罕的行為不具備這種地位。然而,就舊的約所代表的預表階段而言,亞伯拉罕的行為被上帝賦予了一種類比之類型的價值(an analogous kind of value)。[225]
克萊恩的論述中有幾個要點。首先,請注意,當克萊恩把亞伯拉罕的順服說成是「獎賞的基礎」(meritorious ground;或直譯為「有功績的理由」)時,他將這種措詞理解為是「類比於」基督在舊的約的啟示的「預表階段」中所賜下的完全順服的價值。也就是說,亞伯拉罕的順服在任何時候都是得贖者的順服——凡透過聖靈造作的信心與應許的彌賽亞聯合的人的順服。反過來說,亞伯拉罕的順服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與救贖主、耶和華的僕人、中保-彌賽亞的順服混淆。只有基督的順從才能提供適當的盟約功績,從而滿足原始的行為之約的要求並撤銷其懲罰。亞伯拉罕的順服和「功績」的概念充其量只能與基督的真正功績相類比。
其次,克萊恩更精確地說明了亞伯拉罕的順服如何是不完美的,但卻能與基督有功績的順服相類比,他認為上帝賦予亞伯拉罕不完美的順服一種獨特的功能,使他的後代得到祝福。在五旬節前的漸進式救贖啟示時代,上帝圍繞著順服的亞伯拉罕建立了一個國度。
克萊恩在他最後出版的題為《上帝、天堂與哈米吉多頓》的書中,也許更清楚地闡明了亞伯拉罕順服的預表作用。他說到:
創世記第廿二章記錄了另一個情節,在這個情節中,亞伯拉罕傑出的順服行為被說成是耶和華賜給他盟約祝福的基礎:「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第16-18節)。從亞伯拉罕因信稱義的個人經歷來看,這一順服行為證實了他的信心(雅二21及以下;參創十五6)。但從救贖-歷史/末世論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服具有預表意義。耶和華將亞伯拉罕的順服視為基督順服的預言記號,基督的順服為祂的子民賺取了天國。[226]
克萊恩將亞伯拉罕的順服置於「救恩次序」的基本結構中,強調他的順服是「出於信心的順服」(參羅一5;雅二14-26);但同時,他又認為亞伯拉罕的順服具有預言性的預表意義,預示了基督有功績的順服。
與克萊恩早先在《天國序言》中的觀點一致,亞伯拉罕的順服是普遍的、聖靈造作的順服,是每個信徒的特徵。然而,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看,同一種順服具有預表意義。耶和華將預言性的預表功能分配給尋常的、由聖靈造作的信心,預示著基督高峰性的、一次而永遠的順服。
然而,克萊恩擴充了《天國序言》早期的表述,認為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基督順服」的「預言記號」(prophetic sign)。只有後者,即基督的順服,才能為選民「賺得」(merits)末世救贖。作為一種記號,亞伯拉罕的順服必須與它所代表的基督的順服有實質區別。此記號(sign),即亞伯拉罕的順服,與所象徵的事物(the thing signified),即基督的順服,不能混為一談或混淆。亞伯拉罕在每一點上的順服都是在恩典之約下得贖之人的順服。基督在每一點上的順服都是恩典之約下救贖者的順服。亞伯拉罕順服的預言性和預表性強調了亞伯拉罕——得贖者和基督——救贖主之間不可逆轉的區分。
因此,在這些方面,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基督順服的不完美的預言和預表。有了這些限定條件,並牢記這些限定條件,我們就可以繼續前進,進一步體會亞伯拉罕的順服作為基督順服的預言性記號和預表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亞伯拉罕的順服在《舊約》聖經中被賦予了一個獨特的角色:這是一個前提性的預表現實(typological reality),他的後裔和萬民都將因此而得福。就亞伯拉罕的情況來說,一人的順從是上帝所定旨的行為,它預示著眾人的福氣,從而起到預表彌賽亞順從的作用(創廿二16-18)。
亞伯拉罕後裔的祝福與他「順從」耶和華的「聲音」(voice)有關。亞伯拉罕的順服被賦予了將外邦人包括在內的功能。他的順服所具有的預表性和預言性就在於此:一個人不完美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導致了眾人的祝福。當然,克萊恩的推理是,創世記廿二章類比(並預表)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和羅馬書五章,在這兩章中,一人的順服確保了祂所代表之眾人的福氣。
讓我們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的措詞和神學,進一步提煉並澄清克萊恩在既定上下文中談到亞伯拉罕的「功績」時所要表達的意思。亞伯拉罕的順服是由基督的靈造作的(WCF 16.2),雖然在每一點上都不完美(WCF 16.5),但卻因他與所應許的彌賽亞出於信心的聯合而蒙悅納(WCF 16.6)。然而,與此同時,亞伯拉罕的順服也預示著基督的主動順服[active obedience](WCF 7.5),從這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服是一個「預表」,「象徵著」彌賽亞的到來(8.6)。亞伯拉罕「尋常」的順服被分配了一種預表論的功能,暗示了基督順服的主動層面。因為亞伯拉罕憑著信心聽從了耶和華的聲音,所以地上的萬國都將蒙福。上帝悅納亞伯拉罕的「信心順服」必須取決於亞伯拉罕因信與所應許的彌賽亞的聯合。這是WCF第16章中的觀點。上帝接受亞伯拉罕的順服作為使萬國蒙福的行為,這意味著上帝將他的順服作為彌賽亞順服的預表。
回到《天國序言》,克萊恩說,亞伯拉罕以一種具體地預表方式發揮作用,這種方式不僅與道成肉身的聖子有關,也與永恆聖子有關。克萊恩說,亞伯拉罕的工作:
僅僅是一種預表性的指針。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被上帝評價為配得獎賞的亞伯拉罕的順服,充分地象徵著彌賽亞的使命。在創世記十五章中,上帝所宣告的獎賞,針對的是君王的事奉,即搭救臣民脫離耶和華的敵人。在創世記廿二章中,上帝的獎賞針對的是祭司獻祭的事奉。這些順服的行為合在一起,展示了上帝僕人的奉獻職責,包括看守聖所與獻祭之消極和積極的層面。(譯按:《天國序言》,326頁)
順服的亞伯拉罕是忠誠的盟約僕人,他的順服是耶和華僕人的典範,透過順服,祂成為了新的約的擔保人。就像彌賽亞僕人那樣,祂的功績確保了上帝對作為祂「後裔」的多人的祝福(賽五十二15;五十三10-12),亞伯拉罕也是如此,他順服的獎賞就是預表國度對作為他後裔的多人的祝福(參賽五十一2)。然而,實體先於預表。「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八58)。亞伯拉罕的救主後裔早於父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是眾人中的一人,同屬那位的「後裔」,是在彌賽亞一人裏蒙福眾人的一員。[227]
克萊恩認為,這段引文的最後部分非常關鍵:實體先於預表。這意味著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在救贖之約(pactum salutis)——永恆聖子在救贖之約中的順服——的大框架下進行的。從盟約歷史線性發展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是基督的預表,基督是在亞伯拉罕之後降臨的。但如果從與永恆諭令相關的盟約歷史角度來看,亞伯拉罕則是永恆聖子的預表,祂在亞伯拉罕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一旦我們理解了克萊恩思想中的這一結構,我們就能將亞伯拉罕的順從與Logos asarkos(未有肉身的、永恆邏各斯)和Logos ensarkos(有了肉身、成了肉身的聖子)連在一起。亞伯拉罕的順服與永恆聖子在「救贖之約」中的順服一樣,都與產業有關。也就是說,雖然亞伯拉罕的順從是尋常「基督徒的」順從,但他的順從與預表的迦南產業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這正是亞伯拉罕的順服具有預表意義的原因。亞伯拉罕的順服具有預表意義,正是因為它 (a) 為國度子民提供了一個不完美的「基礎」,(b) 與國度子民將要居住的預表領域有關。亞伯拉罕的順服是為了代表聖潔的子民,也是為了以預表的方式確保他們將與耶和華相交的聖潔領域。
然而,請注意,亞伯拉罕的順從與永恆聖子在「救贖之約」中的順從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不連續性。與永恆聖子的順服不同,亞伯拉罕的順服仍然是不完美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一個與彌賽亞聯合的得贖罪人的順服。與永恆聖子的順服不同,亞伯拉罕的順服與預表的國度有關,而不是於末世國度有關。永恆聖子的順服帶來了末世產業。亞伯拉罕只是這類順從的預表。最根本的一點是,與永恆聖子的順從不同,亞伯拉罕的順從是受造物的順從,而不是造物主的順從。
因此,克萊恩將永恆聖子完美的、有功績的順服——原型順服(archetypal obedience)——與亞伯拉罕不完美的、聖靈所賜的順服——複本順服(ectypal obedience)明確地區分開來。正是從這個框架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克萊恩所說的亞伯拉罕的「有功績的」順服與為聖潔子民確保聖潔的預表領域的關係。亞伯拉罕的順從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approximates)永恆聖子有功績的順從。這種近似在於,亞伯拉罕不完美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在為聖潔的子民獲得聖潔領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亞伯拉罕不完全的、由聖靈造作的順服既是永恆聖子在救贖之約中有功績的順服的積極複製[positive replication](縱向關係),也是道成肉身的聖子作為恩典之約的中保的有功績的順服的積極預期[positive anticipation](橫向關係)。亞伯拉罕提供了一個預表的範例,引導信眾去辨別永恆/道成肉身的中保的順從與救贖之約和救恩歷史的關係的複製和預期。這就是克萊恩的基本觀點——他的觀點並不是要與以下事實競爭或削弱這樣的事實,即如果從救恩歷史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從與每個信徒的順從是同等的。克萊恩對亞伯拉罕預表的、「有功績的」順服的讚賞,並沒有破壞他對亞伯拉罕作為出於信心的順服的讚賞(參加三6-9;羅一5;雅二14-26)。
從這一點出發,亞伯拉罕的順服也為以色列人在行為原則下的功績順服提供了原型。在《天國序言》中,他注意到以下幾點:
創世記廿六5(以及在創廿二18最初給亞伯拉罕的啟示中)用到的‘eqeb,即「因為」一詞,表明亞伯拉罕得到的是報酬、獎賞(參詩十九11;箴廿二4;賽五23)。這一點強化了將亞伯拉罕的行為理解為有功績之行為的觀點。此外,創世記廿六5描述了亞伯拉罕的順服,其措詞在創世記的背景下會令人感到驚訝,因為上帝的要求是由一系列立法類別的術語來表明的,它們之後會應用在摩西律法中。在申命記七12中,這類語詞與‘eqeb,即「酬報、報應」(參八20)的組合特別有意思。因此,創世記廿六5很有可能從西奈之約中採用了有關盟約規定的術語,在後者中它描述的是一種受到有功績的行為原則支配的安排,強化了亞伯拉罕的順服同時也被理解為具有功績性質這一要點,以及亞伯拉罕的順服也是他的後裔享受獎賞的基礎。[228]。
從一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從是彌賽亞獨特順從的預表例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亞伯拉罕的順服提供了救贖-歷史的原型,為西奈之約中另一個「有功績的行為原則」的本質提供了依據。我們無需猜測亞伯拉罕與國族以色列之間的聯繫。摩西之約的立法範疇適用於亞伯拉罕「有功績」的順服。此外,亞伯拉罕的順服體現了一種行為原則,具有「功績性」,與「西奈之約」和另一種「受到有功績之行為原則支配的安排」相關聯。只要克萊恩也將國族以色列在西奈之約下的順服解釋為「一種受行為原則支配的安排」,亞伯拉罕的順服與國族以色列的順服之間的統一性似乎就很清楚了。有鑑於此,克萊恩認為摩西之約中的措詞很有可能適用於亞伯拉罕,因此以色列在摩西之約下的國族的順服是亞伯拉罕在恩典之約下之順服在本質上的有機延伸。因此,亞伯拉罕的順服與以色列作為一個國族的順服在類型上並無不同。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都是罪人,他們都是靠著聖靈與彌賽亞的聯合而得到救贖,他們都提供一種與預表的產業有著獨特關係的順服。關於亞伯拉罕對預表國度的順服的討論,為理解以色列對迦南產業的順服的本質提供了基本的救贖-歷史參考框架。克萊恩將這些思考關連在一起,並應用在國族以色列,他說到:
雖然以色列的產業和對應許的持續享有並不是法律上的功績,但國族的集體虔誠與繁榮之間是有關連的。因為舊約的神治國度預示著上帝的完美國度,在這個國度裏,公義與榮耀將合而為一。因此,為了保持預表-預言圖景的清晰,上帝允許以色列人只有在他們,尤其是他們的官方代表,表現出國度適當程度的公義時,才能享受預表國度的祝福。由於以色列人所擁有的任何公義都是救贖她的上帝所賜予的恩典,申命記第廿八章所遵循的原則與行為救贖的宗教就沒有任何相干(見六1-3注)[229]。
以色列人的順從與亞伯拉罕一樣,表現出的公義都是「來自拯救祂的上帝的恩典賞賜」。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色列是亞伯拉罕得贖的後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這個國族在預表國度中的「集體敬虔」和「公義的適當尺度」。公義的「適當尺度」在亞伯拉罕和他的順從中找到了先例。以色列作為預表的上帝兒子,只要他表現出忠誠,他就既按照亞伯拉罕的模式順服,又預表地體現了「上帝完滿成全國度」的聖潔,而這個國度將在彌賽亞降臨時到來。然而,如果國族以色列不忠於耶和華,長久背道,那麼這個預表的兒子就會以關鍵的方式重演亞當的罪孽和被擄,並從迦南聖地遭放逐。
亞伯拉罕與國族以色列之間的連續性在於,聖靈所造作的尋常的順服是在行為原則的背景下發揮作用的,而行為原則把這種順服與預表的產業連在了一起。區別在於亞伯拉罕的順服與預表產業的獲取有關,而國族以色列的順服與產業的維持(順服)或喪失(不順服)有關。以色列如果順從,就會跟隨亞伯拉罕信心與順從的原型,保存預表的產業。如果以色列不順從,就會撇棄亞伯拉罕的信心原型,在預表論的範疇內重演亞當的罪孽與被擄,喪失預表的產業。就以色列的順從與保留預表的樂園土地有關連,而以色列人的不順從與被逐出預表的樂園土地有關連而言,就存在著上帝建立的一種結構,允許複製亞當的罪孽與被擄,並且在恩典之約的摩西施行體系下作出調整,以適應以色列與耶和華的救贖關係。這就是在國族以色列內部,在救贖層面上重新調整後的行為原則的本質,這本質會在預表的層面上運作。
這些觀察設定了國族以色列在與順服的亞伯拉罕、墮落的亞當相比時,以及在與所應許的第二個亞當(基督)相比時的預表處境參數(parameters of national Israel’s typological situation),並闡明了克萊恩思想中的功績問題。亞當作為一個無罪的盟約元首,原本可以提供無罪的順從,從而獲得末世產業。基督作為神人和中保,是唯一一位可以(而且也確實)提供適當的有功績之順服的人,祂的順從滿足了行為之約的要求並撤銷其懲罰,從而為祂的選民賺得了末世產業。如果我們考慮到應用在無罪的盟約元首身上的功績概念,那麼亞伯拉罕和以色列都不可能賺得上帝的祝福。然而,根據主權恩典原則,並為了救贖預表論的益處,上帝在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的情況下規定了一種由聖靈造作的順服,這種順服相對於預表的土地產業具有獨特的功能。
克萊恩的觀點是,雖然亞伯拉罕和以色列都不能提供盟約元首的無罪順服,以確保並永久維持末世產業,但兩者都提供了與獲得或保留與預表國度相關的預表順服的獨特實例。因此,克萊恩似乎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功績概念——分別是盟約功績(ex pacto merit)和預表功績(typological merit)。前者指的是一個無罪的盟約元首所獻上的完美無瑕的順從,它與末世國度的獲取和永久保留息息相關。[230] 後者指的是罪人(透過對所應許的彌賽亞的信心而蒙受恩典)所提供的不完美的順從,它與預表國度的獲得與維持緊密相連。因此,克萊恩並不是要使用在教義史上發展起來的功績語言。相反,他是在將有條件限制的功績語言的應用,擴展到救贖歷史中的人物身上,以便分離出他們與預表國度相關的順服的獨特之處。
總之,可以準確地說,上文概述的預表功績(typological merit)概念是從預表性的闖入(typological intrusion)中產生的,在預表闖入中,「整體上再現了創世時的秩序(然而受到了人類墮落境況的限制,並伴隨救贖進程而產生的調整)」。[231] 預表-救贖的闖入,再加上與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相關聯的救贖預表論,產生了「預表論的」功績概念。雖然可以理解有些人會對克萊恩將預表功績的措詞應用在罪人身上的適切性表示擔憂,但預表性的功績概念本身似乎並沒有違反威斯敏斯特標準。
IV. 利未記十八章5節、行為原則與背道:團體與個人
考慮到這些條件,克萊恩援引利未記十八章5節說道:
利未記十八章5節藉著指出履行盟約規定的人就必活在這些規定中,宣告說,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必須遵行律法的要求,才能享受預表國度的祝福。即使就永恆救贖這方面來說是選民的個體,也會因為各種嚴重違反律法的行為,而從暫時的預表領域中被剪除,來作為懲罰。同樣地,只要以色列國民向他們天上的君王維持適當程度的忠誠,他們就可以集體地在應許之地維持自己的神治國度。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會失去預表國度,就會在那個集體的、預表的意義上失去作為神的百姓的特殊身份。如果他們違背了聖約,就會遭受放逐,在預表的層面上失去蒙揀選的國家身份。[232]
克萊恩的這段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如何將摩西之約中國族的、預表層面的背約與個人層面的背約連在一起。以下的一些觀察可能會幫助克萊恩的讀者澄清這個問題。
克萊恩認為,在恩典之約下,背約是可能的。這種觀點與承認割禮/洗禮兩種聖禮都具有祝福或詛咒雙重獎懲的神學是一致的。在恩典之約中接受上帝主權的人,如果沒有憑著對彌賽亞的信心行事為人,就會面臨按照行為的審判,而彌賽亞會為他們承擔審判。克萊恩說:「此外,新的約的新意並不在於把救贖之約簡化為揀選和保證賜福的原則。它的律法特性也體現在這一點上,即它仍然是一個具有雙重獎懲的盟約……特別是,它既要宣告咒詛,又要執行剪除」。[233]
從克萊恩的表述可以看出以下幾點。首先,正因為新的約在個人層面上是可違背的(或譯為可破壞的,下同),所以它不能簡化為揀選和保證祝福的原則。其次,這是因為新的約與舊的約中恩典之約的表達方式一樣,都具有祝福和詛咒的雙重獎懲。在解釋恩典之約下的背道行為時,這些要點至關重要,因為克萊恩確認,新的約在特定意義上是可以違背的。
由於背道,新的約在個人層面上是可以被破壞的(參來十26-31)。當新的約中的個人沒有支取福音的事實陳述(indicative),沒有憑著在愛中運行的信心而行事為人時,背道就發生了(參羅一5;加五6)。這個個體就會被從盟約群體中剪除,受到盟約詛咒的制裁,失去末世產業。
換一種說法,新的約中的祝福是在一種視條件而定的信心(contingent confidence)中運作的,這信心來自一個因著聖靈所造作的與基督的聯合,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而行事為人的人。這可以用信仰告白的措詞表達為:在與基督的聯合與相交中,透過信心和順服來「善用我們的洗禮」(參見 LC 167;或譯為:使我們的洗禮更真實有效)。克萊恩談到了恩典之約附加之條件的一種形式,這是因為主對聖潔的要求在其表述上是一致的。[234] 割禮和洗禮這兩個聖禮在表達所應許的事實陳述的同時,也以這樣一種方式表達了對歸神為聖與聖潔的要求的升級和完善。最後,為了支持這些觀點,克萊恩訴諸恩典之約的雙重獎懲,無論在舊的約還是新的約的施行中都適用。
現在,讓我們以克萊恩的聖禮神學為指導,簡要地擴展這一討論。在解釋以色列的被擄和失去國家的揀選與恩典之約下的背道的關係時,我們可以說,割禮在適用於國族以色列的「未受割禮的心」時具有審判的功能,其方式類似於它在適用於以色列(或在亞伯拉罕之約或新的約中)個人的「未受割禮的心」時具有的審判功能。摩西和先知們訴諸這個事實,即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有一顆未受割禮的心(申十16;耶四4)。這種未受割禮的情況使這個民族受到盟約的威脅性獎懲,就像未受割禮的心使個人受到恩典之約的威脅性獎懲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表達了一種威脅性的獎懲——根據犯罪行為的審判。
那麼,差別在哪裏呢?國族以色列與新的約中的個人之間的區別在於,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在預表象徵的層面上承受著割禮的詛咒獎懲。這一現實的實質在於,以色列的背道在一個獨特的、預表化的情境中招致了割禮的詛咒獎懲,從而使這個民族喪失了預表國度。就像個人背道會失去末世產業一樣,背道的國族以色列也會失去迦南預表國度的產業。這一現實可以透過類比教會對個人的懲戒來理解——不同的是,以色列經歷的是一種團體形式的教會懲戒,其重點是失去預表-象徵性的迦南產業土地。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包含了與預表國度中的審判有關的行為原則的本質。在這兩種情況下,背道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會受到行為原則的審判。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如果沒有對耶和華表現出適當的忠誠,就會導致個人或國族承擔審判,後者的形式是被逐出迦南。而且只要以色列在國族層面上還受到割禮詛咒的威脅,就是亞當的罪的一種重複(repetition),也是對亞伯拉罕的信心-順服的一種否定(repudiation)。以色列背道的獨特性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審判乃是以預表的喪失土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為以色列的民族背道增添了獨特的特徵,歸根結底,這種背道在救贖歷史上重演了亞當的罪孽與被擄。
新的約中的洗禮的意義延續了這一盟約審判的主題。洗禮與割禮一樣,都帶來雙重獎懲。克萊恩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洗禮和割禮的意義有著徹底的對應關係。兩者都是歸盟約的主為聖的認信誓言記號(confessional oath signs),都象徵著他最終的救贖審判,既有定罪的可能,也有稱義的可能」。[235]
顯然,克萊恩認為割禮和洗禮的誓言記號(oath signs)之間具有連續性。二者都是雙重獎懲的記號與印記,都有待靠著聖靈造作的信心與彌賽亞的聯合來支取(或不支取)福音的事實陳述。
然而,鑒於這種統一性,克萊恩也發現了從割禮到洗禮這一過程中重點的轉移。克萊恩說到:
隨著舊約的割禮轉移到新約的洗禮(約翰的洗禮在這方面也是過渡性的),盟約啟示的重點確實從審判的咒詛方面轉移到了伸冤的一面。這一變化反映了救贖歷史的動向,從定罪的施行轉到了公義的施行。儘管如此,新約中歸神為聖的記號並沒有因為這種重點的轉移而將咒詛的元素排除在外,就像舊約的儀式並沒有僅僅因為舊約中歸神為聖的儀式是以定罪和死亡為特徵,而將伸冤限定條件(vindication-qualification)排除在外一樣。[236]
克萊恩正在探究兩種情況的差異:一種情況是將割禮的記號施作在缺乏內心割禮的國族,結果是被擄,以及失去預表的土地產業(類似於上文描述的亞當被逐出伊甸園);另一種情況是新約中重點的轉移,即盟約的記號施作在內心受割禮的一群百姓身上(參羅二26-28)。最顯著之重點的轉變可以解釋從定罪的施行轉變到公義的施行。最顯著之重點,因著新的約中的背道,成為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最顯著之重點,因著割禮和洗禮,象徵並印證著同樣的屬靈現實(與彌賽亞的聯合),並提供同樣的雙重獎懲,即離開了彌賽亞的咒詛,以及在彌賽亞裏的祝福。克萊恩在救贖史上大書特書,他發現了一種轉變,這種轉變擺脫了將以色列人的順從與預表的土地維護聯繫在一起並給這個民族帶來定罪/被擄的預表行為原則。取而代之的是,焦點轉向了基督,祂在原型行為原則下(protological works principle),在生命與死亡之中的有功績的順服,確保並維護了選民永恆的國度產業。
克萊恩的聖禮神學成為一個關鍵的聚焦透鏡,我們可以透過它來區分並聯繫集體與個人的背道行為,並更清晰地認識摩西之約的本質、國族以色列的順服,以及亞當的罪孽和被擄在以色列長期背道行為中的預表-象徵性重演。
V. 舊的約與新的約的體系與「可破壞性」
克萊恩區分了整體上牢不可破的新約體系(new covenant order;或譯為新約秩序),以及個人對新約的背道。新約作為一個整體,是牢不可破的,與摩西統治下有關行為原則和土地持有的舊的約不同。關於整體的新約體系,他說到:
隨著摩西體系的廢除,在主與教會立的新的約下啟動了彌賽亞時代的第二層國度。耶利米在談到未來要訂立的新的約時(耶卅一31-34),將新的約與在西奈所立的約(即新的約中與預表國度有關的層面)進行了鮮明的對比。他將舊的約描述為是可違背的,事實上以色列人已經違背了舊的約,這意味著舊的約是憑行為原則來繼承產業的。他斷言,新的約將與妥拉之約不同。它將是牢不可破的;它將是對福音恩典與赦罪的施行。因此,我們在肯定新的約與摩西管治體系的基礎福音層(foundational gospel stratum)以及亞伯拉罕應許之約的連續性的同時,也必須承認新的約與舊的約(在其預表論層面上)之間在行為與恩典上的不連續性,也就是耶利米所強調的差異。[237]
讀者應該仔細注意克萊恩是如何從整體盟約體系的角度來談論這個問題的,而不是在討論他在其他地方所肯定的個人背道的狹義問題。這一區別很重要。克萊恩確認,恩典之約中的個人可以被嫁接進或嫁接出新的約,因此從狹義上講——就恩典之約的新約施行中的個人而言——新的約是可以違背的。他說到:
羅馬書第十一章透過橄欖樹的意象向我們說明了兩個階段之間的兩種連續性。一種是選民、屬靈後裔的連續性(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但與之相伴的是作為一種制度的盟約群體的連續性,它比選民的範圍更廣。橄欖樹作為一個整體代表的是立約制度,而不是揀選,這一點從一些(可惜很多)猶太枝子被折斷,以及不繼續接受上帝恩惠的外邦人枝子受到同樣的砍伐威脅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出。[238]
雖然新的約作為一種體系——在「救恩歷史」(historia salutis)中獨樹一幟、高峰的體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新的約中的個人卻有可能被約並被剪除。新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是牢不可破的,儘管該體系中的個人可能會違背新的約而隨流失去。
理解這一特徵,就像理解我們所論述的其他特徵一樣,在克萊恩的全部著作中保持一致,有助於避免混淆摩西在國家層面上對恩典之約的施行與新約對同一恩典之約的施行之間存在的差異。兩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可以無條件地違背,而後者則是無條件地不可違背。這種說法過於簡單化,無法抓住克萊恩的神學觀點。相反,從國族、預表論的層面來看,舊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是可以打破的,因為國族以色列因背道和悖逆而被放逐。雖然新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在「救恩歷史」(historia salutis)的層面上是不可破壞的,但在「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層面上卻是個人可以違背的。
VI. 反對意見
A. 摩西之約中與國族以色列有關的誓言
對克萊恩的解讀如果對上述區分不夠敏感,就會把他的觀點說成是「實質再版」,而不是「施行再版」。也就是說,一些對克萊恩的解讀沒有注意到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之間,在與預表國度有關的「有功績的」順服方面所存在的深刻連續性。這種疏忽會對本節所介紹的克萊恩的解讀產生許多反對意見。我們將考慮一些反對意見,並做出簡要回應。
值得強調的是,克萊恩在關鍵文本中談到了西奈之約中的行為原則,它與恩典-信心-應許的原則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 [239] 此外,克萊恩指出,在西奈之約中起誓的是以色列,有些人可能會堅持認為,這支持了這樣的觀點,即該約是源自伊甸園之再版的毫無恩典的行為原則。
對此,我們需要記住克萊恩所闡釋的與亞伯拉罕有關的行為原則的本質和功能。正是透過亞伯拉罕,表現出「有功績」的「行為原則」提供了一個歷史範疇,在救贖層面重新調整了以色列神治國度中的行為原則。無論是獲得(亞伯拉罕)還是維持(以色列)預表國度,墮落後的行為原則都將聖靈造作的順從與預表國度連在一起。與亞當行為之約的一種類比浮現出來,但也僅僅是類比而已。亞當身上沒有救贖恩典,而亞伯拉罕和以色列卻有救贖恩典。
此外,我們必須記住克萊恩思想中的行為原則是如何根據罪的現實和救贖預表論進行調整的,它適用於以色列的起誓。以色列人向耶和華起誓是作為「亞伯拉罕後裔」的國族的一部分,他們要表現出亞伯拉罕所表現出的那種類型的順服。換句話說,他們所起的誓並不是一種重新復原的(repristinated)伊甸園裏墮落前的誓言,也不是效法亞當的順服。恰恰相反,它是以亞伯拉罕為原型、具有救贖歷史意義的誓言,旨在保存預表的土地產業。
正是這一透過亞伯拉罕繼承的原則統管著以色列這個國族的「次要層級」。鑒於這一現實,預表的國度是透過以色列作為一個國族藉著聖靈造作的順服來維持的。
換句話說,克萊恩的觀點是,並不是基督所作的擔保(suretyship)永久確保了預表國度的維持;而是以色列的順從、民族忠誠或宗教忠誠發揮了這種作用。克萊恩說到:
如果他們違背盟約,就會遭到放逐,在預表層面上失去蒙揀選的國族身份。當然,這就是實際的結果。以色列人成了「羅阿米」[譯按:Lo-Ammi,「非我民」]。失去在摩西之約中賜予以色列人的這種國族揀選的身份,這個事實迫使所有承認上帝在救贖恩典中的主權的人,認識到摩西之約中確實存在著行為原則。很明顯,基督作選民中保的這種主權恩典,與舊的約下的預表範疇(包括其國族性的揀選與祝福)之間的關係,和它與個人蒙揀選進入救贖的終極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相同的,後者是恩典之約所有施行方式的目標。在摩西所確立的體系,也就是在次要的、預表的層面上,以基督具有功績的成就為基礎的主權恩典,並無法保證以色列會持續不斷擁有國度的祝福。毋寧說,這是以色列人順服律法的行為所賺得的獎賞。[240]
基督的擔保在關鍵方面適用於以色列這個國族,就像適用於亞伯拉罕一樣(ordo salutis)。然而,同樣的擔保並不能確保預表國度體系(historia salutis)的永久安穩。基督的順服並不能確保迦南地的產業永久不變。相反,只要以色列人跟隨亞伯拉罕的信心與順服,包括上文概述的限定在救贖層面的功績概念,國度的產業就會由以色列人保持。如果以色列不順服,預表國度本身就會瓦解——而基督完美的順服所保障與維護的實體國度卻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克萊恩將這種經過仔細限定和細微差別的情況視為行為原則,而正是這一原則與以色列的起誓誓言有關。
在克萊恩的思想中,我們需要理解的是基督的順服與以色列的不順服所喪失的預表國度之間的區別。克萊恩的觀點是,以色列的處境與墮落的亞當體系相關聯,不順從就會喪失產業——這與基督的順從賺得末世產業的方式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因此,雖然基督作為擔保人的恩典在「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層面上為以色列的順服提供了保障和能力,但在「救恩歷史」(historia salutis)的層面上,祂的順服並不能確保預表國度的永恆維持。如果祂的擔保人身份確實永遠確保了預表國度,那麼這種體系就會永遠存在。預表國度的體系並沒有存到永遠,因為它的永久維持並不是植根於基督的擔保,而是植根於國族以色列的順從。這也許就是克萊恩行為原則神學的核心觀點。
這一見解解釋了克萊恩為何強調以色列所起的誓與繼續享有預表國度的祝福有關。由於以色列人向上帝起誓與繼續享有預表國度的產業有關,所以是以色列人的順從而不是基督的順從維持了預表國度。也就是說,以色列的順從——與亞伯拉罕的順從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與預表國度的維持有著獨特的關連,而不順從則會失去預表國度。克萊恩認為,正是這種情況解釋了為什麼預表國度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會喪失,而實體國度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卻不會喪失。預表國度的維持與國族以色列——預表之子——的順從息息相關;而實體國度的完滿成全與永久維持則與基督——末世聖子——的順從息息相關。正是在這裏,克萊恩將摩西之約在預表論層面與新的約之間的鮮明對比放在了一起。不理解這個微妙之處會導致對克萊恩的誤讀。
B. 克萊恩對功績術語的混亂使用
對克萊恩行為原則神學的另一個反對意見是他對功績措詞的不當使用。人們擔心的是,克萊恩的用法是新穎的,在解釋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的順從的本質時會把水攪渾。在這一點上,上文所做的區分值得回顧。
第一個可能證明為有用的區忿是已經概括論述過的無罪盟約元首(亞當和基督)的順服與藉著與中保聯合而得到救贖的罪人(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的順服之間的區分。在前者中,要求無罪的盟約元首按照行為之約的條款完全順服,是達到末世晉升目的的手段。需要注意的關鍵是,如果不能按照盟約的條款完全順服,就會立即受到審判。不完全的順從是無法被悅納的。就後者而言,與WCF第16章一致,為了基督的緣故,不完全的順服是在恩典的原則下蒙悅納的,可以起到獲得或維持預表國度的作用。但這種順服並不像無罪的盟約元首那樣與末世的晉升聯繫在一起。不完美的順服(和不順服)也不會立即受到審判。這意味著克萊恩所理解的「預表功績」與他所理解的與無罪的盟約元首有關的功績在類型上肯定是不同的。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區分是,克萊恩並不是把他的「預表功績」概念應用在「救恩次序」(ordo salutis)是,而是應用在「救恩歷史」(historia salutis)上。也就是說,功績的概念並不著眼於獲得永恆救贖的個人,而是著眼於預表的土地產業所附帶的不可重複的聖靈造作的順從事例。因此,這需要我們理解的是,相對於功績的歷史神學討論的一種語詞與概念的區分(a word-concept distinction)。克萊恩並不是要把功績的措詞應用在亞伯拉罕或國族以色列身上,就像改革宗傳統(包括克萊恩本人)把功績的概念應用在亞當或基督身上那樣。相反,他將一種高度限定的功績概念應用於不完全順服的獨特事例(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這些事例以獨特的方式與預表國度在盟約層面(covenantally)緊密連在一起。
因此,克萊恩的「預表論功績」(typological merit)概念是一個必須與正當功績和盟約功績實質區分開來的「第三類功績」(tertium quid;直譯:第三件事)。
總結與結語
克萊恩提供了「救恩歷史」(historia salutis)與「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一種整合,試圖從聖經的角度對救贖歷史中關鍵人物的順從與末世產業(亞當或基督)或預表國度(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的關係作出細緻入微的解釋。部分基於他與諾曼·雪佛(Norman Shepherd)的神學和葛雷格·邦森(Greg Bahnsen)的神治國度倫理學(theonomic ethics)進行論戰,克萊恩為自己的觀點增添了細節與清晰度,儘管這些人物並不總是能被我們識別出來。
根據這種解釋,克萊恩並不主張與救贖恩典的存在相競爭的「功績原則」,無論是在亞伯拉罕還是在國族以色列的情況下都是如此。克萊恩並不否認聖靈造作的信心是亞伯拉罕或國族以色列「有功績的」順服的特徵。克萊恩並不主張在以色列的神治國度下恢復與亞當的行為之約;相反,他主張根據罪和救贖的現實作出調整的行為原則。這一原則透過亞伯拉罕得到了救贖性的重新調整,當應用在(背道的)國族以色列時,最終重演了(reenacting)亞當的罪和被擄。
克萊恩對行為原則的理解源於天國在迦南(縱向)的救贖性和預表性闖入,以及亞伯拉罕(橫向)的救贖性重新調整的行為原則。這兩個特徵共同提供了一個救贖性的行為原則,它將聖靈所帶來的罪人的順從與獲得或維持預表的土地產業聯繫在一起。
行為原則將以色列人能否繼續留在迦南地與他們對盟約之主的忠誠表現緊密關連在一起。如果以色列人沒有表現出這種忠誠,就會失去預表國度。藉著割禮與洗禮這兩個聖禮的意義和功能,可以把國族以色列的背道與教會中個人的背道連在一起。在對國族以色列的咒詛中,割禮的記號的獨特應用涉及到預表國度的喪失——這一特徵並沒有出現在恩典之約之亞伯拉罕施行體系與新施行體系中的個人背道上。
克萊恩的觀點也許最適合被描述為與亞當立的行為之約的結果在國族以色列範圍內的一種施行方式的重演(administrative re-enactment),並根據罪、恩典和救贖預表論的現實情況進行了調整,結果是被逐出迦南的產業-土地。雖然對克萊恩的其他解讀表明他贊同與亞當所立的行為之約的實質再版,但本章所展開的論證思路,尤其是亞伯拉罕作為集體以色列順服的本質的救贖歷史參考框架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表明情況並非如此。
附錄:約翰·慕理與魏司堅對摩西之約的看法
下文將概述魏司堅(Geerhardus Vos)和約翰·慕理(John Murray)的摩西之約神學。這裏的目的並不是要像對克萊恩那樣深入探討。相反,我們的目的是對二者進行闡釋和分析,以便從基本結構上展示它們與克萊恩的關係。我們將看到的是,在慕理那裏,恩典之約在救贖應用中的統一性(unity)幾乎是唯一的焦點。慕理正確地指出了恩典之約各種施行的統一性,魏司堅和克萊恩都肯定了這一基本的神學觀察。然而,魏司堅的闖入神學(theology of intrusion)和他對救贖預表論的發展在慕理那裏卻沒有得到重視。魏司堅指出了救贖性闖入和預表論如何在以色列的國族認同層面上交匯,並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我們可以透過它來理解被擄的救贖歷史意義。克萊恩正是廣泛地發展了魏司堅的這些主題。
I. 約翰·慕理
本節將簡要介紹慕理關於亞伯拉罕和摩西恩典之約的神學。與克萊恩相比,我們會發現克萊恩和慕理在摩西之約的本質上有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共同神學觀點。慕理堅持認為,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都是恩典之約的主權施行——這一點克萊恩完全同意。慕理強調,恩典之約在亞伯拉罕時期的施行和摩西時期的施行,在建立時都是單邊的,但在實施時卻是雙邊的,主要在於與耶和華的聯合與相交。慕理主要關注的是救恩次序(ordo salutis)在亞伯拉罕和摩西施行中的統一性。與這一重點相適應,他很少關注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的獨特預表論特徵,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每種施行所共有的盟約相交關係(covenantal communion bond)的本質上。
A. 亞伯拉罕之約
慕理認為,亞伯拉罕之約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慕理指出「耶和華藉著莊嚴的獎懲向亞伯拉罕確認了他將繼承迦南地這一應許的確定性」。[241] 其次,從這一特徵中衍生出「關於守約和背約的內容(創十七9、10、14)」。[242] 前者強調上帝單方面確立了恩典之約;後者強調在與主的聯合與相交中,這種盟約安排的雙邊執行(bilateral outworking)。
關於第一個顯著特點,慕理指出,亞伯拉罕之約顯示了救贖之約的本質。他說:「盟約是一種神聖施行,它的起源、建立、確認和實現都是神聖的。不是亞伯拉罕從被劈開的動物中間穿過,而是神的靈。神的靈代表上帝。因此,上帝的行動是單方面的。這是給亞伯拉罕的確認,而不是從亞伯拉罕而來的確認」。[243] 亞伯拉罕之約是由上帝以自我咒詛誓言的形式以至高主權施行的,這就強調了「神聖的主權和信實對所立之約的影響,並賦予其特性」。[244]
慕理進一步解釋說,亞伯拉罕之約的核心是與耶和華的聯合與相交,他寫道:「……盟約所賜的親密性和屬靈性。祝福的本質是上帝要作亞伯拉罕和他後裔的上帝,即《舊約》中特有的應許,『我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作我的子民』。簡而言之,這包括與耶和華的聯合與相交」。[245] 恩典之約的核心在於與耶和華的聯合與相交,是彼此接納(mutual embrace)的神聖盟約。
恩典之約的亞伯拉罕施行體系中突出的第二個關鍵特徵是盟約的相互性。慕理指出:
關於……遵守聖約的必要性和禁止背約的警告,我們不能壓制這樣的推論,即遵守聖約的必要性與聖約本身的豐富性、親密性和屬靈性是相輔相成的……(亞伯拉罕[之約]涉及最高層次的宗教關係,即與上帝的聯合與相交…… 因此,守約不僅與作為恩典施行的盟約本質不相容,它的發起、確認和實現都是神聖的,而且它是由所涉及的宗教關係的親密性和屬靈性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我們對所賜予的至高恩典的理解越深刻,就越需要接受者對等的忠誠。[246]
慕理的觀點是,亞伯拉罕之約的單向性——它的單方面建立——是為了與耶和華的聯合與相交。亞伯拉罕之約的目標是尋回並完成上帝與祂用寶血贖回的子民之間的盟約相交關係。盟約關係的屬靈特性要求接受者既需要以主權主權分配的恩典,又需要對等的忠誠。直截了當地說,「人遵守盟約的必要性並不妨礙神聖的神恩獨作的恩典施行(divine monergism of dispensation)」。[247]
因此,慕理明確指出,「毫無疑問,如果受益人不履行某些條件,就無法享受或維持盟約的祝福以及盟約所包含的關係」。[248] 然而,慕理很快又加以限定,說這些條件並不是盟約本身(即盟約的建立)的條件,而是上帝的主權恩典「繼續享受這種恩典和建立這種關係」的條件。 [249] 因此,亞伯拉罕之約在特定意義上是有條件的;正如慕理所主張的,「信心、愛心和順從的相互回應,離開了這些,享受盟約的祝福和盟約的關係就是不可想像的。總之,守約的前提是盟約關係已然建立,而不是建立盟約關係的條件」。[250]
有鑑於此,破壞恩典之約讓我們看到了一些非常獨特的東西。他說:「背約所破壞的不是賜予盟約的條件,而是完滿結果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consummated fruition.)」。背約使盟約無法在末世的福氣中結出果實。破壞恩典之約,最終就是放棄在與主的聯合與相交中讓彼此的接納盡善盡美。
B. 摩西之約
慕理在論述摩西之約時,首先提醒讀者摩西之約的條件性這一關鍵點。他說:「首先,我們必須記住,有條件的應驗(conditional fulfilment)並不是摩西之約所特有的。」 [251] 他這樣說是考慮到他對亞伯拉罕之約在其實施過程中是有條件的這一確切含義的廣泛論述。鑒於上文所述亞伯拉罕之約是有條件的,慕理的理由是,條件性本身「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理由,讓我們用不同於亞伯拉罕之約的術語來解釋摩西之約」。[252] 換句話說,兩者都是恩典之約的不同施行方式——兩者都是單方面建立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又是雙邊的。
摩西之約成全了對亞伯拉罕和始祖的應許(出二24),基於這一事實,慕理認為「關係的屬靈性是亞伯拉罕之約的中心,也是摩西之約的中心。『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上帝』(出六7;參申二十九13)」。[253] 換言之,「兩者都考慮到了最高層次的宗教關係,即與上帝的聯合與相交」。[254] 他繼續說到:「因此,我們決不能壓制或貶低這些重要的考慮因素,即摩西之約是以色列人從埃及被解救出來之後與他們訂立的……摩西之約也是恩典的主權施行,由上帝發起、確立、確認和應驗」。[255]
這一觀點的必然結果如下:
人們常常假設,摩西之約所規定的條件將摩西時期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類別裏,一方面是恩典,另一方面是要求或義務。實際上,摩西之約與亞伯拉罕之約所要求的守約和聽從上帝聲音的必要性,並無原則上的差異。在這兩種情況下,基調都是聽從上帝的聲音並遵守盟約(參創十八17-19;出十九5、6)。[256]
慕理試圖維護恩典之約的亞伯拉罕施行體系和摩西施行體系之間的基本連續性。他認為,每一個盟約都是由上帝以至高主權施行的,但每一個盟約的共同關注點都是救贖性的聯合以及在彼此接納的神聖關係中與耶和華的相交。在恩典之約的兩種施行方式中,彼此的接納(mutuality of embrace)以及藉著信心與順服來延續盟約中的相交關係都是核心。
慕理的基本關切是避免「嚴重錯誤」(grave error),即摩西之約是一個行為之約,與亞伯拉罕之約「完全不同」。換句話說,慕理試圖避免摩西之約的本質是與亞當訂立的行為之約的實質再版這一觀點。慕理不僅考慮到了實質再版,而且還考慮到了試圖從摩西之約中剔除恩典的古典時代主義。他想讓讀者明白,在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層面上,存在著一個單一的、有機的、逐步實施的恩典之約。因此,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在「救恩次序」的層面上實質上是一體的。
慕理在其關於恩典之約的評論中,尤其是在摩西施行體系中,沒有闡釋的是迦南地作為預表的樂園-土地,在這個範圍內也存在著救贖性的闖入(redemptive intrusion)的概念,以及這種闖入對國族以色列在救贖歷史中的獨特性的神學意義。這並不是說慕理不相信在神治國度中的闖入和救贖預表論,而是說他在處理摩西之約時沒有展開這些特徵。
這又是如何將他與克萊恩相提並論的呢?如果把克萊恩看作是實質再版的倡導者,那麼慕理的評論就會以能夠想像的最強烈的方式與克萊恩的觀點背道而馳。然而,如果我們把克萊恩解釋為施行再版的倡導者,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慕理和克萊恩在摩西之約的實質方面是基本一致的。然而,我們也可以說,克萊恩在闖入、救贖預表論以及以色列以救贖的方式重演亞當的罪孽與被擄等問題上遠遠超越了慕理。
II. 魏司堅(Geerhardus Vos)[257]
魏司堅的著作比慕理早很多年,他同意慕理關於摩西之約中「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基本神學觀點,但與慕理相比,他更關注「闖入」(intrusion)和「救贖預表論」(redemptive typology)的現實。
也許對克萊恩摩西之約神學的最好概括就是,它試圖提煉魏司堅並擴展其基本見解。事實上,在《大君王條約》和《天國序言》中,克萊恩使用的措詞和概念似乎都源自魏司堅的《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克萊恩將迦南視為來世聖潔的闖入,以及克萊恩將以色列的順從視為「表達的適當性」(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的概念,都出現在魏司堅的著作中。
魏司堅認為,國族以色列的順從與保留迦南地的繼承特權之間存在聯繫。他說:
那麼很顯然,在那個節骨眼上,遵行律法並不是得到生命產業的功德基礎。生命的產業唯獨基於恩典,保羅也非常強調恩典是救恩的基礎。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反駁說,遵行律法即便不是人領受救恩的基礎,也是保留所承受的特權產業的基礎。當然,這裏不能否認其中有真實的關聯。但是,猶太教徒犯了一個推理上的錯誤,就是認為這層關連必須是功德性的(meritorious),也就是說,如果以色列人是通過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兒繼續保有耶和華所賜予的恩賜,那麼他們就必定有功勞,因為是以絕對的公正賺得了這些恩賜。但是遵行律法與保有恩賜之間的這種關聯卻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別。它不屬於功績的法定範疇,而是屬於表達之適切性(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的象徵-預表範疇。[258]
克萊恩在《大君王條約》和《天國序言》中都呼應了魏司堅的表述,他在其中提到了規範耶和華與國族以色列之間關係的「主權恩典原則」。他認為,以色列必須對他們在天上的君王保持「適當程度的民族忠誠」。此外,克萊恩還談到,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迦南這個「預表-象徵」的神聖領域。
除上述觀點外,魏司堅還明確指出迦南作為闖入,以及以色列在救贖歷史中所具有的獨特預表-象徵功能。他說:「神治國度預表了上帝完美的國度……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居住地預表了上帝子民屬天的完美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堅持絕對遵行上帝律法聖潔的理想」。[259] 魏司堅認為,在以色列的神治國度中出現了一些獨特的東西——即它是一個體現了屬天現實的屬地場所。居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是來世聖潔的預表呈現(typological presentation)。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曠野到安息,從世俗領域到聖潔領域,這一動向標誌著救贖歷史中與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地緊密相連的獨一無二的內容。
魏司堅將背道與被闖入的迦南聖地的獨特關係連在一起,顯示了他對救贖預表論的敏感。他說:「當背道普遍發生時,他們就不能留在應許地了。當他們失去了預表聖潔地位的資格時,他們就在事實上(ipso facto)失去了預表蒙福地位的資格,也必被擄去」。[260]在神治國度範圍裏的信徒和非信徒都是如此。以色列作為一個國族失去了繼續留在預表的應許之地的資格。因此,魏司堅發現,在以色列國家層面上,與土地產業和被擄有關的事情是獨特的、不可重複的。國族層面的背道導致預表國度的喪失。
魏司堅還將「救恩次序」中個人層面的背道與「救恩歷史」中以色列被擄時期的獨特情況連在一起。他指出:
這意思並不是說,每一個以色列人在祂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上,都必須做到完美,而上帝的持續眷顧也因此而中止。耶和華主要與國族打交道,並透過國族與個人打交道,正如祂如今在恩典之約中,祂與信徒及其世世代代的子孫打交道一樣。上帝子民之間有一種一體性(solidarity),但只要整個國族保持忠誠,同樣的原則也能抵消個人犯罪的後果。整個國族及其代表領袖的態度是決定性因素。[261]
因此,恩典之約下的個人背道與恩典之約下的國族以色列之間存在著一種類比。以色列作為一個國族,因背棄恩典之約而失去了上帝的眷顧。魏司堅在論述國族以色列的背道以及由此導致的預表象徵性土地產業的喪失時,表現出了對闖入和救贖預表論獨特特徵的敏感性。
魏司堅的論述朝著克萊恩日後詳盡發展的方向前進。魏司堅將「上帝子民屬天的、完美地位」之聖潔的闖入,歸屬於總體而言的神治國度。他還提到了「表達的適當性」,它起到了維持土地產業的作用,而持續背棄盟約則會導致土地產業的喪失——這是國族以色列神治國度獨有的特徵。[262] 魏司堅與慕理在恩典之約的摩西施行體系下信徒所經歷的恩典的統一性問題上基本一致,但魏司堅在神治國度中發展了預表論和闖入的特徵,這些特徵標明了國族以色列身份在迦南疆界內的獨特性和一勞永逸的功能。克萊恩對闖入和救贖預表論的表述顯然取決於魏司堅對這兩者的敏感度。
然而,克萊恩對與亞伯拉罕有關的救贖預表論的理解超越了魏司堅,這反過來又幫助他發展了亞伯拉罕和國族以色列的行為原則神學。從《大君王條約》到《天國序言》和《上帝、天堂與哈米吉多頓》的發展,轉向了澄清以色列的行為原則,因為它在亞伯拉罕及其作為基督預表的獨特順服中找到了起源。與雪佛(Shepherd)和邦森(Bahnsen)的爭論為發展救贖預表論的獨特特徵提供了論戰背景,這些特徵擴展了魏司堅的許多見解,但並沒有削弱慕理認為摩西之約實質上是恩典之約的堅持。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與雪佛和邦森的爭論之後,亞伯拉罕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為適用於國族以色列的行為原則提供了救贖歷史原型,這一歷史人物形象的發展與慕理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的早期著作有著有機的連續性。
因此,當我們把克萊恩與魏司堅和慕理連在一起時,最好把克萊恩理解為一位神學家,他保留了慕理對恩典之約中亞伯拉罕和摩西施行體系的統一性的堅持,同時又推進了魏司堅關於救贖闖入和預表論的見解,說明了在經過實質修改的救贖場景中獨特地重演(re-enact)了亞當的罪孽和被擄的特徵。
(下一章)
4 thoughts on “信正長老會(OPC)「再版」研究委員會報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