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wo Kingdom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Pt. 1: Introducing the Antagonists
作者:Brad Littlejohn
October 25, 2012
誠之譯自:https://politicaltheology.com/kingdoms-guide-perplexed-pt-1/
(譯按:這一系列網文後來被編輯成為一本書,The Two Kingdom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由The Davenant Press出版,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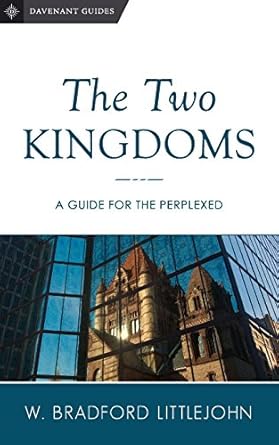
過去幾年,保守的北美改革宗神學的狹小世界被其經常發生的內訌撕得四分五裂。更寬廣的神學世界很少有機會注意到這些往往令人不快的場面,而值得政治神學家關注的場面也確實不多。然而,最近關於「改革宗兩個國度神學」的爭論卻是政治神學,尤其是其新教實踐者所忽視的一個問題。這場運動與一些古老的問題進行較量,包括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創造與救贖的關係、自然律與聖經的關係,等等,而將保守派改革宗——通常以俗話所說的「把頭埋在沙子裏」(譯按:即逃避現實)而聞名——推向了有關基督教信仰在自由派公共領域中的角色的當代辯論之中。
值得慶幸的是,自從大衛·范竹能(David VanDrunen)的《自然律與兩個國度》(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Social Thought)一書出版以來,人們並沒有完全忽視這個問題。該書出現在 2010 年約翰·維特(John Witte)的《埃默里大學法律與宗教研究》(Emory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w and Religion)叢書中。除了主要期刊上常見的禮貌性報導(有些天真地對該書的權威外觀印象深刻,有些則審慎地提出批評)之外,詹姆斯 史密斯(James K.A. Smith)在《加爾文神學期刊》(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上,以及最近詹妮弗·赫德(Jennifer Herdt)在普林斯頓大學自然律研討會上對該書進行了實質性的批評。前者提出了奧古斯丁的「兩座城」來替代范竹能的「兩個國度」,後者則對其自然律的論述進行了批判。然而,對改革宗「兩個國度」教義的歷史主張(這是范竹能之提案的核心)的詳細審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而我正是希望在這個由五部分組成的系列(一、當前形勢;二、路德到加爾文;三、加爾文到胡克;四、胡克到洛克;五、它為什麼很重要)中向讀者介紹這場辯論。
那麼,這個主張、這一運動究竟是什麼呢?它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神學家邁可·霍頓(Michael S. Horton)和歷史學家達里·哈特(Darryl G. Hart),他們大多與加州埃斯孔迪多的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Seminary in Escondido, CA)有關聯,因此有人稱它為「埃斯孔迪多神學」(The Escondido Theology)。與神學中的大多數運動一樣,要理解它,首先要瞭解它所反對的是什麼。R2K(譯按,即reformed two kingdoms;改革宗兩國論)理論家們把目光對準了保守改革宗和福音派世界中的惡魔三人組(trio of boogeymen):神治論(theonomy)、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和福音派(儘管范竹能擴大了攻擊範圍,把激進正統派、新興教會(the emergent church)和 N.T. 賴特等各種敵人也包括在內)。其中,神治論(又稱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m)可能是普通讀者最不瞭解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神治論在改革宗中曾風靡一時,但最近已逐漸式微。「神治論」提出全面恢復《舊約》中的民事律,將其作為基督教建造現代社會的藍圖。神治論者聲稱,任何不符合這一點的政治神學都是對不信者的妥協,都是把人的話語置於神的話語之上。
新加爾文主義得到更多主流人士的認可,包括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A. Smith)、小約翰·維特(John Witte)和尼古拉斯·沃爾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等著名政治神學家,尤其在荷蘭改革宗中,他們是主導力量。不過,與R2K理論家們特別相關的是其積極分子,教義派成員,他們在保守教派和機構中佔據著一個稍微自我封閉的圈子。他們的特點是信奉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的公共神學,並透過二十世紀荷蘭哲學家赫爾曼·杜伊維爾(Herman Dooyeweerd)以及亨利·斯托布(Henry Stob)、艾爾·沃爾特斯(Al Wolters)和哥尼流·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等北美追隨者加以傳播(儘管後者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並得到了神學家們的認同)。概括地說,這一傳統的口號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決心以「基督教世界觀」的基本思想為基礎,「轉化」(transform)社會的各個「領域」(spheres)和機構。與神治論不同,新加爾文主義更關注哲學上的「基礎動機」(ground-motives)而非律法上的規定,關注的是靈性而非儀文,但它也可能具有類似的凱旋主義者(triumphalist)的熱情。(譯按,關於新加爾文主義,這篇網文稍微詳細地作出了一些解釋,值得參考:我們是否需要一場新加爾文主義的復興?)
當然,「福音派」(Evangelicalism)是這三個敵人中最不成熟的一個,但也是霍頓(Horton)和哈特(Hart)等人撰寫的更受歡迎的 R2K 級著作的主要目標。美國福音派被指責為,要為低教會論、貶低制度性教會、貶低教會事工和聖禮的價值負責任;他們也被指責為天真的聖經(字面)主義(biblicism),即認為每一個問題都有聖經經文可以解決;還被指責為好戰的政治激進主義(譯按:即俗稱的「宗教右派」)。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基督的國度與世俗政治的混淆,因為福音派堅持把對聖經的特殊理解強加給選民和政治家。當然,這樣說來,對福音派的這種批評並不新鮮,埃斯孔迪多神學家之外的許多人也會有同感。在哲學思想上更加成熟,但仍然經常是凱旋主義式(和哲學上的還原論)的新加爾文主義,同樣受到了許多政治神學家的合理懷疑;至於神治論,除了在最核心的改革宗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會認為它需要駁斥。因此,改革宗兩個國度運動的一些主要關注點——即希望重新強調教會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對聖經權威和適用性的過度宣稱的懷疑,對在世俗和政治結構中實現福音規範的能力持健康的冷嘲熱諷態度,並強調信徒與非信徒在世俗生活中廣泛的共同點(commonality)——似乎都是有益的,也得到了大多數頭腦清醒、神學思維縝密的評論家的認同。
那麼,我們有可能會問,「有什麼問題嗎?」(Where’s the beef?)好吧,就像大多數以反動為基本原理的運動一樣,改革宗兩個國度運動在抵制這些聖經字面主義和凱旋主義訴求時,也受到走過頭了的誘惑。為了澄清基督教信仰與政治的這些不合時宜的模糊關係,R2K運動提出了一整套廣泛且緊密相關的二元論:屬靈國度與公民(或「現世/temporal」或「共同/common」)國度、教會與國家、救贖與創造、永恆與現世、耶穌基督與造物主上帝、聖經與自然律。制度性教會是基督的屬靈國度,唯獨在其中,以耶穌基督為元首,為永恆救贖進行救贖的工作。另一方面,生活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國家)是上帝公民國度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中沒有信徒與非信徒之分;這一領域只是為了暫時維護受造界的秩序,由作為造物主的上帝管理,並以自然律而非聖經的規定為準則。
這種表述,很明顯是一種會引起許多神學家警惕的模式。這種模式可能引發的擔憂,尤其是新教徒的擔憂,包括:有形教會概念中過度實現的末世論,以及其他地方未充分實現或不存在的末世論;創造與救贖的二分法,而不是將後者視為前者的整體應驗;基督徒的救贖和重新定位的生活並沒有在他所有的天職中體現出來,在救贖主基督和造物主上帝之間的二元論中所存在的基督論和三位一體神學,基督升天神學的欠缺,以及將自然律和聖經視為相互排斥而非相互解釋的奇怪觀點。
毋庸諱言,R2K 理論的支持者們對於這些二元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壓制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有多緊密,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極端的是達瑞·哈特(Darryl Hart),他似乎經常暗示,基督徒的救贖身份在教會的四面隔牆之外沒有任何意義,以信仰為基礎的原則在公共場合也沒有任何地位,[1] 儘管范竹能最系統的論述《活在上帝的兩個國度》(Living in God’s Two Kingdoms;P&R 出版社,2010 年)似乎要溫和得多。馬太·圖寧格(Matthew Tuininga)提倡的形式則最為溫和,他顯然堅持需要在文化和政治中作出有聖經依據的基督徒見證,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R2K 的各種二元論,他正在小約翰·維特(John Witte. Jr)門下攻讀加爾文兩個國度神學的博士學位[2]。
鑒於 R2K 理論家都是相當堅定的認信主義者(即他們堅持嚴格遵守改革宗信仰告白的表述),這項工程必然具有重要的歷史維度——證明這種兩個國度模式是改革宗的標準教義,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時期。傳統上,「兩個國度」思想一直與路德和路德宗聯繫在一起,而范竹能則聲稱,加爾文採納了路德的這一教義,並確實使其得到了更令人滿意的發展,加爾文的徒子徒孫始終將其作為一種手段,既抵制了伊拉斯謨派的企圖,想讓國家對教會發號施令,也抵制了(范竹能承認不太一致的)神權國度派的企圖,想讓教會對國家發號施令。正如這一「不那麼一致」的讓步所表明的,這並不是一個乍看起來很有希望的更新工程(a project of ressourcement)。畢竟,包括加爾文在內的所有早期改革派都極力強調需要一個基督教的地方行政官來支持教會並執行十誡中的兩塊石版。有些人,尤其是英格蘭和蘇格蘭的一些人,走得更遠,他們主張《聖經》中的律法對公民政體繼續具有約束力,這與近代的神治論者很相似。令范竹倫感到不便的是,後者實際上是那些最明確地發展了「兩個國度」教義的人,在其他方面與他自己的教義最為相似(例如,無條件地將制度化教會與「屬靈國度」相提並論,以及將救贖主的王權與造物主的王權對立起來)。事實上,即使是他自己也承認,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的南方長老會,范竹能才真正找到了他基本滿意的改革宗兩個國度範式。
其主張就談到這裏,關於這場辯論又如何呢?鑒於除了在改革宗敵人的想像中之外,神治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改革宗陣營對 R2K 運動的反應並不顯著。另一方面,福音派過於分散、過於龐大,以至於沒有被最近這一輪的批評所困擾。在博客上、期刊上,以及最近出版的幾本長篇評論書籍(《埃斯孔迪多神學》[(The Escondido Theology]和《國度分離》[Kingdoms Apart])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反對聲音來自各種新加爾文主義者。他們尤其熱衷於批判創造與救贖的二分法,更傾向於把救贖說成是創造的「恢復」(restoration)或「轉化」(transformation),並淡化自然對墮落人類的可及性或價值。這些批評家中的許多人或多或少都樂於把歷史觀點讓給范竹能,而只是批評宗教改革家們過於二元對立的兩個國度概念(儘管最近在歷史方面出現了一些反彈)。[3]簡而言之,他們所關注的是,兩個國度神學提供了一種未充分實現的末世論,在這種末世論中,基督國度眼下的範圍被低估了。
在我看來,更有趣的是反面的批評—,即認為在事實上,兩個國度神學以一種從根本上有悖於新教的方式,將基督屬靈的治理與可見教會的制度結構相提並論,從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過度現實化的末世論。這種批評,我們可以稱之為「古典兩國論」(classical two-kingdoms)觀點,與新加爾文主義者不同的是,它主要針對范竹能論述中的歷史問題,指責他從根本上歪曲了早期新教的教義,而早期新教教義是繼路德之後從兩種治理(two governments)的角度來理解兩個國度的,即內在的和外在的、屬靈的和現世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可見的權威領域或機構。正因為改教家將教會的制度形式和公民行政官(civil magistracy)都理解為現世國度的一部分,他們才能利用這一教義來支撑非常接近伊拉斯謨派的政教關係。根據這種解讀,范竹能對兩個國度的解釋更多地是來自蘇格蘭約老會(Scottish Covenanters)和伊麗莎白時代的清教徒等激進分子,而不是來自主流改教家。[4] 這些早期兩國論教義的倡導者將按立的牧師認定為基督的代治者(vicars of Christ),由於將神職人員的權柄納入政治領域,因此傾向於一種新教皇主義(neo-papalist),這似乎與當代 R2K 倡導者所追求的嚴格分離主義截然相反。對古典兩國論的批評者認為,范竹能等人關於新教神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出現之間的聯繫的論點大體上是正確的,但他們認為,埃斯孔迪多工程由於混淆了兩個國度的本質,陷入了試圖在本質上不自由的教義基礎上建立起自由的政治安排這一無可救藥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古典新教的兩個國度教義,例如基本上(in nuce)在路德那裏發現的,在加爾文那裏被模棱兩可地採納了,並在理查·胡克(Richard Hooker)那裏得到廣泛的發展,為以神學為依據的有序多元主義(theologically-informed ordered pluralism)提供了更好的資源,這種多元主義既提供了現代自由的好處,又沒有將基督教的規範性主張從公共廣場上撤走。[5]
正如最後一段中充滿同情的描述所暗示的那樣,我屬於後一種「古典兩國論」的批評者群體中的一員,並相信我們的論述無論在擴展我們對宗教改革神學和早期現代政治思想的歷史理解方面,還是在為當代政治倫理提供建設性論述方面,都有很大幫助。因此,在接下來的三篇文章(將在未來幾周內發表)中,我將從這一視角講述兩個國度神學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發展形式,但我希望沒有過度的偏見,並試圖在相關的地方指出范竹能和圖寧格的不同解釋。在最後一篇文章中,我將進一步闡述這些不同說法在神學和政治上的利害關係。
(下一篇)
注:
[1] 哈特本人的觀點有時仍難以捉摸,因為這些觀點通常是在歷史論述中隱晦地闡述的,如《美國新教失落的靈魂》(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rotestantism)(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世俗信仰》(A Secular Faith)(Ivan R. Dee, 2006)和《從葛培理到佩琳》(From Billy Graham to Sarah Palin)(Eerdmans, 2011)。要全面瞭解哈特未經審查的真實觀點,請參閱他在Oldlife.org 博客上發表的許多與兩個國度相關的文章。
[2] 在過去一年裏,馬特·圖寧格(Matt Tuininga)對兩個國度的神學進行了大量的討論,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討論可以在這裏、這裏(譯文)、這裏(譯文)和這裏(網路上已經找不到此文)找到。我自己對他的歷史性和建設性主張的參與可以在這裏、這裏、這裏,以及最後也是最廣泛的這裏找到(這些文章在網路上已經找不到了)。
[3] 尤其可參閱科內爾·維內馬(Cornel Venema)和吉恩·哈斯(Gene Haas)在《分離的國度》(Kingdoms Apart)一書中發表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的在線樣本見此處。我對 Venema 一文的回應見此處。
[4] 史蒂文·韋奇沃思(Steven Wedgeworth)首次在在線期刊《Credenda/Agenda》上公開發表了這一批評思路,他在此處為達瑞·哈特(Darryl Hart)的批評進行了辯護。隨後,韋奇沃思和他的同事彼得·埃斯卡蘭特(Peter Escalante)在多篇在線文章中闡述了這一批判,其中包括他們的兩部分大型文章(此處和此處)「約翰·加爾文與兩個國度」。另請參閱我最近發表的「再次陷入困境,第二部分:厘清兩國論」。
[5] 關於這些觀點,請參閱埃斯卡蘭特對達瑞·哈特(Darryl Hart)的回應:「一致與混亂:兩種兩個國度」, 以及我即將發表的文章:“Sola Scriptura and the Public Square: Richard Hooker and a Protestant Paradigm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Messer and Paddison, eds., The Bible: Cultu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T & T Clark, 2013).
2 thoughts on “兩個國度:給困惑者的指南(一):介紹對手們(Brad Little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