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wo Kingdom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Pt. 2—From Luther to Calv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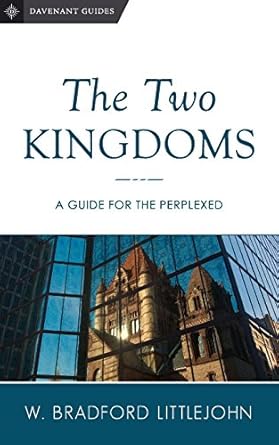
作者:Brad Littlejohn
October 25, 2012
誠之譯自:https://politicaltheology.com/kingdoms-guide-perplexed-pt-2-from-luther-calvin/
(前文)
從歷史上看,任何關於兩個國度教義的討論都必須從路德開始。當然,「兩個」(twoness)的主題從一開始就滲透到基督教的政治神學傳統中——「這世界是由兩……統治的」——這一點似乎很早就很清楚了。不過,儘管我們可以從奧古斯丁的雙城神學或格拉西烏斯(Gelasius)的雙劍神學中找到先例,路德的兩個國度卻不能視為與這兩種神學等同。雖然它們與中世紀的「內庭」(forum internum)和「外庭」(forum externum)之間的區別(譯按:這兩者是中世紀天主教會認為管轄罪孽的不同機構,分別管轄人的內在思想與公開行為)有更多關係,但它們仍然是路德神學與眾不同的獨特產物,因為它們直接建立在他「因信稱義」(sola fide)教義的基石之上。
在大量的二手文獻中,這種與稱義教義的關聯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這些文獻往往帶有現代思想的政治化偏見,過快地將路德的國度解讀為教會和國家這兩個必須嚴格區分的機構。當然,任何對路德有敏感認識的讀者都不得不承認,路德的理論絕不止於此,但許多人堅持認為,路德的理論就是這樣設想的。在《自然律與兩個國度》(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一書中,范竹能(VanDrunen)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路德的兩個國度理論視為他將要敍述的改革宗版本的先驅(他認為改革宗的兩國論版本很明顯是關於這兩種制度的理論),儘管後來的批評使他和他的盟友越來越不試著將路德作為他們的模式的始祖。
威廉·賴特(William Wright)在他最近出色的研究《馬丁·路德的兩國論》(Martin Luther’s Doctrine of the Two Kingdoms)中反對這種傾向,他呼籲我們回到最優秀的學者們一直以來所認識到的內容上來——路德的兩個國度教義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全面的框架,是他對上帝、人和社會的理解的基礎,其前提是這位改教家對人活在上帝面前(coram Deo)和人活在人面前(coram hominibus)的基本區分。簡而言之,它源於稱義的教義以及路德著名的「同時是義人與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概念,即他堅信表相領域與屬靈現實領域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奧秘且無形地統治著良知的國度,任何人類權威都不敢插手充當這一統治的中間人;我們唯有藉著信心才能參與這個國度,因此我們絕不能被蒙蔽,將其與外在的行為或儀式相提並論。也許比「兩個國度」(zwei Reiche)更好的說法是「兩種政權(two governments)」(zwei Regimente)。屬靈政權是基督藉著祂的話語及聖靈在人的良知中進行內在統治的政權,即恩典的領域;而屬世政權(weltliche Regimente)則是基督藉著律法管理人的一切外在事務的治權,在其中,祂不是直接並立即作工,而是透過屬世的管理者和機構的「幼蟲[larvae]」(「面具」)作工。只有蒙揀選的人才會經歷前者;後者則是他們與未重生者共同經歷的。
由此可見,把任何屬於實證領域的機構[empirical institution](包括教會)都說成是屬靈國度是行不通的,當然,把任何生活領域都說成是世俗的也是行不通的。人類生活並不是一幅二維的地圖,在這幅地圖上,兩個國度被畫為一道分界線,劃分出兩個管轄範圍;更確切地說,人類生活是一幅二維地圖,公民國度與之有著共同的邊界(coterminous),而屬靈國度則可以說是這幅地圖的第三個維度,一種垂直的、朝向上帝的關係,它使所有其他維度都充滿了活力。教會本身尤其如此,在路德看來,教會與稱義的信徒一樣,都受制於「既是義人又是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這一自相矛盾的二元對立。就其在上帝面前的隱秘身份而言,教會是「屬靈國度」,是人所看不見的,但在充滿活力的福音宣講和聖禮施行中卻具有可見的形式。就其可見的制度層面而言,教會作為一個必須組織起來、舉行儀式和進行管理的聚會場所,是路德所說的「政體」(polity)領域的一部分,是人類權威領域的一部分,它與家庭和民事法官等更世俗的業務(concerns)共同佔據著這一領域。
與這一教義密切相關的是路德關於基督徒自由的教導,這一教導從一開始就貫穿著同樣的雙重辯證法——「(因著信心)基督徒既是全然自由的眾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但(因著愛心)又是全然順服的眾人之僕,受所有人管轄」。(free lord of all, subject to none/dutiful servant of all, subject to all)在上帝面前,基督徒的內心不受任何人類權威的調解,也不受人類權威命令的良心約束。但正是由於這種內在的自由,基督徒在對外的領域中樂於接受對鄰舍需求的順從(也正因為如此,對人類權威的順從)。外在事物是「無關緊要的」(adiaphora)事情,與救贖無關,在這些事情上,人類法律可以指揮信徒的行為,但不能左右他的良心。因此,當路德堅持基督徒的自由並沒有推翻政治權威時,這並不是因為他小心翼翼地將其限制在一個被稱為「教會」的範圍內,在這個範圍之外,良心可以受到約束,而是因為這兩個政權——良心政權和行為政權——在本質上是無法比擬的。
以上所述可能表明,路德的兩個國度教義對政治神學並無意義——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談論它呢?事實上,它至少在兩個方面對西方政治理論的未來具有深遠的意義。首先,由於拒絕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教會的教導職分可以擁有任何政治權力,路德的教義就顛覆了中世紀的政治秩序,使公民行政官(civil magistrate)成為司法權威的唯一擁有者。事實上,只要教會本身必須採取制度性的和司法的形式(路德在早期的理想主義之後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那麼教會本身就落在基督徒行政官(Christian magistrate)的監督之下,平信徒行政官的身份不再是教會領導權的障礙。尤其是墨蘭頓,他將路德的教義系統化,認為行政官可以行使權力,並在教會的無關緊要之事——外在秩序、政體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禮儀問題上要求人的順服。
但是,如果說路德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將權力集中到王公手中的作用,那麼這並不像許多流行的甚至是學術界的說法所認為的那樣,為專制主義鋪平了道路。恰恰相反,路德的「兩個國度」教義的第二個影響是明顯的自由主義,因為它不僅取消了教會的等級制度,而且取消了所有人類的權威。行政官不再是教會屬靈權威的執行者,不能對良心提出要求,不能對永恆事務發表意見。此外,由於不再有任何權威的世俗仲裁者來確定良心的公正界限,因此,如果行政官試圖超越限制其權力的「無關緊要的事」(adiaphora)領域,基督徒個人在原則上可以作為法官,對其行政官的命令作出判決。當然,在地方行政長官以「無關緊要之事」方式下達命令的權威與個人良知決定何時逾越了「無關緊要之事」界限的權威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值得慶幸的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這種緊張關係被證明是一種創造性的緊張關係,在未來的兩個世紀中激發了新教的政治思考。
但我們必須把故事向前推進,因為宗教改革的內容遠不止路德。在慈運理的蘇黎世宗教改革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改革,只是在術語和概念上有所不同。無論是慈運理還是他的繼任者或布靈格,都沒有用「兩個國度」來表述他們的神學,也不贊同路德嚴格的律法/福音二分法,這意味著他們更願意從《舊約》中尋求指導。這意味著,蒙召要像新的約西亞一樣負責教會改革的「敬虔王子」(the godly prince),要在他的「眾先知」——聖道僕人——的指導下,在他們對一個歸正了的社會的概念中站在絕對的中心位置。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肩負改革重任的「敬虔王子」並不反對路德宗,瑞士人也不缺乏路德的兩個國度教義的基本原則。對他們來說,因信稱義、基督徒的自由和聖經的全備性等核心教義也起到了在基督對良知的屬靈管理以及他由人類代治者對民事和世俗事務的統治之間打入一個尖銳楔子的作用。路德宗和改革宗在這些問題上的兼容性可以從彼得·馬蒂爾·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的思想中看出,他是一位意大利改革家,改革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英國(他對英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蘇黎世度過的,他強有力的政治神學將蘇黎世濃厚的希伯來主題與路德宗和墨蘭頓的「無關緊要之事」(adiaphora)和兩個國度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如果說路德與蘇黎世在這些方面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後者不像前者那樣強調「基督徒的自由」。
加爾文和他與奧科蘭帕狄烏斯(Oecolampadius)和布塞爾(Bucer)所代表的改革宗傳統中的紀律派(disciplinarist)也是如此。這些人雖然在原則上堅持所有信徒的祭司身分和教會宣講聖道、非司法性的本質,但他們發現有必要讓神職人員監督的教會紀律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重洗派信徒要求建立一個更加明顯純潔的信徒團體的回應,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成聖和稱義的新強調的自然發展。雖然這些改教家都不否認路德堅持區分這兩者的必要性以及稱義的絕對優先性,但隨著福音教義的深入人心,要求信仰在信奉新教教義的人中結出善果似乎越來越有必要。在強調這一點的同時,「無關緊要之事」教義的重心也發生了變化:成聖不能說真的「與得救無關」,因此,任何有助於得救的事物也不能說「與得救無關」。雖然路德從未否認過「律法的第三重用途」,但其他改教家卻越來越強調這一點,他們認為聖經是指導基督徒個人和集體行為的準則。從這個角度來看,「無關緊要之事」的範圍縮小了,因為那些由聖經決定的事情不能真正被視為無關緊要,而聖道僕人作為聖經教師的角色也擴大到包括對道德的監督和譴責。
加爾文是最成功地將這些新重點納入神學綜合體並在社區實踐中加以實施的人,因此,范竹能和其他人在加爾文身上發現了一種新的、更加制度化的兩國論神學形式的出現,這並不奇怪。他們認為,對於加爾文及其繼承人來說,「屬靈政權」現在與聖經本身一樣全面,而且由於涉及外在秩序和行為,必須有獨立於公民政府的外在中保和統治者。然而,如果是這樣的話,基督徒的自由教義似乎就岌岌可危了,因為正如范竹能(VanDrunen)在他的論述中明確指出的那樣,現在良心似乎要服從屬靈國度中的人類中保。
在接下來的部分中,我們將更仔細地研究加爾文。我們認為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站在路德一邊的,並將特別關注英國的宗教改革,在那裏,兩個國度教義的對立形式(各自都聲稱自己是基督教自由的最佳守護者)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
關於資料來源的說明:顯然,上述論述將許多極具爭議的論點和解釋濃縮成了一個非常簡潔的形式。為了避免繁瑣的注釋使這篇入門級的論述變得冗長,我省略了所有具體主張的出處。不過,以下文獻對論證尤為重要,建議進一步閱讀:F. Edward Cranz,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uther’s Thought on Justice, Law, and Society; John Witte, Jr., Law and Protestantism; William F. Wright,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W.D.J. Cargill Thomps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Luther; Pamela Biel, Doorkeepers at the House of Righteousness: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Zurich Clergy; Bernard Verkamp, The Indifferent Mean: Adiaphorism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to 1554; P.D.L. Avis, The Church in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W.J. Torrance Kirby, The Zurich Connection and Tudor Political Theology.如果您想瞭解更多細節或想與我爭論任何解釋觀點,請在下面發表評論,也歡迎給我發電子郵件:w.b.littlejohn@gmail.com,越多人討論這些問題越好。
2 thoughts on “兩個國度:給困惑者的指南(二):從路德到加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