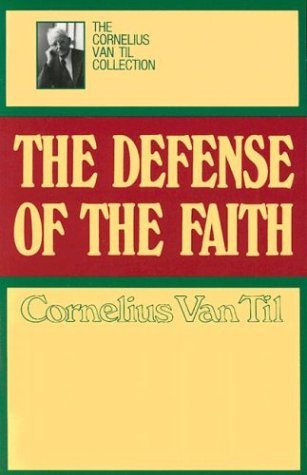
《信仰的護衛》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作者: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
誠之譯自: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Philadelphia, 1955), 31–50.
第三章 基督教知識論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坦率地宣稱,作為基督徒,我們在聖經中找到了我們所信仰的內容,即上帝的話語。我們從聖經中汲取了關於上帝、人、基督、救恩和末世論的教義。作為改革宗基督徒,我們希望向人們展示,他們所需要的是改革宗神學,而非羅馬天主教,甚至也非某些較低層次的福音派更正教。
當我們試圖說服人們接受聖經所啟示的教義體系之真理時,我們談論的是我們的基督教人生觀。我們將這種基督教人生觀細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基督教本體論(或譯為存有論[theory of being])、基督教知識論,以及基督教倫理學或行為論。我們必須將基督教人生觀與非基督教人生觀明確區分開來。基督教與非基督教人生觀之間所有差異的根本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基督徒敬拜並事奉造物主,而非基督徒則敬拜並事奉受造物。透過人類始祖亞當——首先的人、全人類的代表——的墮落,所有人都成為敬拜受造物的人。但藉著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以及聖靈將救恩施作在祂的子民身上,那些蒙揀選的人已經學會(儘管只是在原則上)敬拜並事奉造物主,勝過敬拜受造物。他們現在相信聖經所提供的實在論(theory of reality)。他們現在相信上帝是自足的,相信宇宙萬物都是上帝所創造的,相信人類在歷史之初的墮落,以及藉著基督而來的「萬物的更新」。
但是,擁有一個基督教知識論與擁有一個基督教本體論同樣重要。一個人不可能在擁有其中一個的同時卻沒有另一個。現代思想主要關注知識論。因此,作為基督徒,我們將發現有必要將基督教知識論與現代形式的非基督教知識論對立起來。即便如此,我們仍須清楚表明,我們的知識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我們的本體論如此。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能單獨就知識本身進行思辨。我們不能在探問「我們如何知道」的同時,不去探問「我們知道什麼」。我們再次引用《基督教護教學》:
我們感到不得不從聖經中汲取我們關於實在的本質(nature of reality)的概念。人們會欣然承認,我們所呈現的這種實在觀,只能基於權威來接受。我們所呈現的這種存有觀,除了在聖經裏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聖經被如此嚴肅地對待,以至於我們甚至沒有留下任何已知的實在領域,可以用來對比在聖經裏臨到我們的啟示,或將其作為衡量標準。我們已經將聖經本身視為真理的最終標準。
不用說,在大多數研究哲學的人的眼中,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殺。難道我們不應該借助人類自身的理性來思考實在和知識的本質嗎?接受權威對生命的詮釋,只有在我們研究過所接受之權威的根基之後,才是可行的。但如果我們必須判定權威的根基,我們就不再是基於權威來接受權威了。只有當我們已經知道某個權威有權宣稱其權威時,它才能成為我們的權威。而這只有在我們預先了解該權威的本質時才可能發生。因此,我們在探究之初,已經預設了一種關於存有的理論(=本體論)。如此一來,我們就無法公正地聆聽對立的觀點。
辛格博士(Dr. Edgar A. Singer)在其《經驗與反思札記》(Notes o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一書中的論述,體現了對我們立場的一種現代反對方式。1 辛格博士告訴我們,哲學的任務是追問:我們如何知道?換句話說,根據辛格的說法,認識論的問題可以而且必須在不涉及本體論問題的情況下被提出。
辛格博士的這個立場站得住腳嗎?為了論證起見,假設我們所描述的那種上帝確實存在。那麼,這樣一位上帝難道沒有權利以權威的口吻向我們說話嗎?如果我們說,知識的問題與存有的問題是獨立分開的,難道不正是在排除知識問題本身的一個可能的答案嗎?如果上帝的存有正如我們根據聖經的見證所發現的那樣,那麼我們的知識只有在與祂的知識相符合的程度上才是真知識。說我們在探問知識的本質時不需要探問實在的本質,這並非保持中立,而是實際上排除了對知識問題的基督教答案。
辛格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對知識問題的基督教答案,這一點從他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所肯定的事實中可見一斑。他說,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詢問那些被認為擁有知識的人(第5頁)。他甚至沒有考慮過要向一位其意見可能比他人更有價值、甚至凌駕於其他人的意見之上的權威尋求幫助。在樂園(伊甸園)中,夏娃盡可能地向那些被認為擁有知識的人尋求幫助。上帝和撒但都以知識淵博而聞名。顯然,上帝不認可撒但的知識,撒但也不認可上帝的知識,但各自都對自己的知識深信不疑。因此,夏娃不得不權衡這些名聲。對她來說,這是一個關於「我們如何知道?」的問題。
夏娃所面對的問題十分棘手。上帝告訴她,如果她吃了禁果,她必定死。從人數來看,贊成的一方只有一位,二反對的一方也只有一位。因此她無法用人數來解決名聲的問題。她自己必須透過動議和投票來決定這個名聲問題。上帝宣稱祂是造物主。祂宣稱祂的存有是至高無上的,而撒但的存有則是受造的,因此依賴於上帝的存有。撒但實際上是在說,她根本不必關注這個存有的問題。撒但告訴她,她應該自行決定「我們如何知道?」,而不必問「我們知道什麼?」。牠說,對於牠和上帝對她吃了禁果後會發生什麼的詮釋,她應該保持中立。夏娃在回答知識的問題時,確實忽略了存有的問題。她說,她會盡可能收集多那些以博學著稱的人的意見,然後對這些不同觀點給予公平的聽證機會。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夏娃的行為並沒有真正迴避「我們究竟知道什麼?」這個問題。她意在言外地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她對上帝的存有做出了否定。她否認了上帝的存有是終極的存有。她由此實際上肯定了所有的存有在本質上都處於同一層次。
同時,她也對「我們如何知道?」這個問題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她說我們獨立於上帝而知道。她宣稱上帝的權威應該由她自己來檢驗。因此她逐漸取代了終極權威的位置。毫無疑問,她將要透過經驗和對經驗的反思來檢驗上帝的權威。然而,最終的權威將是她自己。
由此看來,我們所闡述的存有論,與聖經作為上帝之權威啟示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聖經所談論的這樣一位存有者,除了以絕對權威說話之外,別無他法。歸根究柢,我們必須在兩種知識論之間做出選擇。一種理論認為,上帝是最終的上訴法庭(court of appeal);另一種理論則主張,人才是最終的上訴法庭。
對於上述所說的,我們必須在此補充一點。罪在人的心思意念裏造成了最具毀滅性的影響。人已經「死在過犯和罪惡之中」(譯按:弗二1)了。若要人承認上帝的合法地位,人就必須重生。若不重生,人就不可能看見「天國」。
罪惡會在知識領域顯露出來,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一切詮釋的最終上訴法庭。他會拒絕承認上帝的權威。我們已經藉著亞當和夏娃的敘事來說明了有罪之人的態度。人宣告了自己的自主權凌駕於上帝之上。
這意味著,在人必須為自己尋求的整體圖景中,他必須以聖經作為最終的上訴法庭。他仍然從自然中學習,但自然所教導的必須與聖經所教導的建立關聯,方能獲得正確的理解。
壹、上帝對祂自己的知識
因此,正如我們有雙層實在論,我們也有雙層知識論。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們已經論證過,上帝是自我決定的(self-determinative)。祂沒有與自己相對立的非存有,祂不需要也無法在任何程度上以非存有來詮釋自己。祂是全知的。祂之所以全知,是因為祂作為自足的存有者(a self-sufficient Being)的本質。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補充說,上帝存有之本質要求祂擁有完全徹底的自我意識。上帝的存有與祂的自我意識幾乎是重疊的(coterminous=共享邊界)。
強調這一點很重要。有些人說上帝的存有是絕對的,但上帝的意識卻受制於一連串的瞬間(succession of moments)。引入這個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上帝如何在我們的現世世界中感知一連串的瞬間。亞米念派神學家華生(Watson)在其《神學要義》(Theological Institutes)中,就上帝對時間事件的知識作了這樣的推理:「因此,把時間長短(duration)的概念應用在上帝身上,只不過是把應用在我們自身的觀念加以延伸;若要求我們將其設想為本質上不同的事物,就等於要求我們設想不可想像的事物。」針對華生所提出的觀點,我們觀察到:如果我們要以理解時間與永恆之關係的可能性,作為永恆理論的檢驗標準,那麼我們很快就會徹底拋棄上帝的永恆性。一個我們應該能夠理解其與時間之關係的永恆,恰恰會破壞上帝作為自我決定之存有者的永恆性。如果我們為了理解上帝與時間的關聯,而將時間或一連串的瞬間引入上帝的意識中,我們就必須反過來問自己,上帝的意識與上帝的存有之間有何關聯。因此,出於我們將一連串瞬間引入上帝的意識中的同樣理由,我們也必須將一連串的瞬間引入上帝的存有之中。
與此相反,聖經將上帝描繪為是全知的,是完全擁有自我意識的。在上帝裏面,不存在有何隱藏的可能性的深幽之處,是祂自己的意識所未曾探知的。在非存有裏面,也不存在任何事物是需要上帝等待,才能自己完全察覺到的。我們對上帝與時間之關係的理解的限制,不應成為我們對上帝知識本質的衡量標準。
應當注意的是,只有當我們堅持上帝的存有與意識是重疊的,我們才能避免泛神論。如果知識和存有在上帝裏面(就祂自己而言)不是同一的,祂就不得不依賴於自身之外存在的事物。如此一來,上帝的意識就受制於現世性的現實,進而上帝的存有本身也受制於現世性的現實。
確實,泛神論者斯賓諾莎(Spinoza)也可能使用「在上帝裏面,知識和存有是同一的」這樣的說法。然而,使我們的立場與斯賓諾莎或任何其他非有神論思想體系完全對立的,是這樣的一個事實:當我們在上帝裏面將知識與存有視為等同時,我們只是在談論上帝自己的存有與祂的知識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指祂對祂所創造之物的知識。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正是基於在上帝裏面,知識與存有具有同一性,我們才將人類能夠進行述謂(human predication)的盼望寄託於此,並對此懷抱堅定信念。
因此,我們毫不猶豫地強調,上帝擁有、並且就是完全的內在連貫性(internal coherence)。就上帝自己的位格而言,主體就是知識的客體。因此祂對自己的知識完全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暗示上帝必須經歷一個審視自己並發現有關自己之資訊的過程。作為受造物,我們不可能擺脫與我們所使用的一切詞語相伴的時間性聯想。但在哲學領域,「分析性的」(analytic)這個術語已經逐漸演變為「自我依賴」(self-dependence)的觀念。分析性知識與綜合性知識(synthetic knowledge)不同,指的不是藉由參照存在於認知者之外的事物而獲得的知識。上帝認識自己,不是透過將自己與任何外在事物——甚至不是與祂自身之外的非存有——進行比較和對比。祂藉由一個純一的、永恆的洞見行動認識自己。因此在上帝裏面,實在的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就是實在的。
貳、上帝對世界的知識
在前面的幾個段落中,我們談到了上帝對自己的知識。現在我們要探討上帝對祂自身之外事物的知識之本質。在這裏我們必須轉向創造論。上帝從亙古就有一個創造宇宙的計劃。我們可以粗略地、類比地將其比作承包商為他即將建造的房屋所繪製的藍圖。承包商拿到藍圖時,房屋還沒有蓋好。對他而言,某件事物的觀念與該事物的現實並不相同。同樣,上帝從亙古就有一個宇宙的觀念。斯賓諾莎會由此推論說,因此宇宙從亙古就已存在。他正是以此來運用他把所有現實[Reality](包括上帝和宇宙)與所有理性[Rationality]視為等同的原則的方式。與此截然相反,我們身為基督徒,持守「創造成為無有」(creation into nothing)的概念(譯按:參第二章,現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我們明確肯定,上帝對宇宙的永恆觀念並不意味著宇宙的永恆創造。
很明顯,我們在這裏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我們一直堅持認為,上帝對祂自己的知識是分析性的。我們一再強調,過去沒有、也不存在任何與上帝對立的非存有,因為非存有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決定上帝的存在。因此,軌道似乎已經鋪設好,正駛向泛神論的岔道。我們已經說過,上帝關於自己的知識與祂的存有是同一的;那麼,上帝對宇宙的知識豈不似乎也應該等同於宇宙的存有嗎?
這個論證與以下的論點相反,後者認為,為了能理解上帝能夠感知宇宙中時間的流逝,我們必須認為在上帝的意識中有一連串的瞬間(succession of moments)。我們已經駁斥了後一種論證,因為它是基於一種非有神論的假設。它假設現世是我們理解永恆的標準,而實際上永恆才應該是我們理解現世的標準。誠然,我們人類經驗肇始於對自己作為現世性存有者的意識。然而,如果我們進行自我意識的思考,就應該明白,我們對自己作為現世性存有者(temporal beings)的意識,預設了上帝對自己作為永恆存有者的意識。我們現在還不打算展開這個論證。但是在這個關鍵點上,我們只想指出,事實上,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知識論之間最基本的對比。基督教以永恆的、具有自我意識的神聖位格來詮釋實在;非基督教思想則以獨立於上帝的存在來詮釋實在。
因此,這個論證——即如果我們認為上帝的存有和祂對自己的認識是同一的,那麼我們也必須持守永恆創造——就必須被駁斥,因為它乃是基於反有神論的假設。有限的受造之物無法理解:上帝如何在不預先決定「外部」現實的本質以至於使其失去意義的前提下,卻擁有對自身之外的全部現實的全然完備的知識。只有有限的理解才會認為,如果對現世的現實進行預先詮釋,時間就會淪為荒謬。只有有限的理解才會從「在上帝裏,存有和對祂的存有的知識是同一的」這個論述中,推導出決定論(determinism)的結論。
因此,如果我們要以有神論的方式進行推理,那麼,有限的心智就不能成為可能與不可能的標準。唯有神聖心智才能決定一切的可能。如此,我們得出結論,上帝對宇宙的知識也是分析性的。上帝對宇宙的知識取決於上帝對自己的知識。上帝按照祂為宇宙制定的永恆計劃創造了宇宙。因此,宇宙的存在本身取決於上帝對宇宙的知識或計劃。誠然,上帝將宇宙和人類視為存在於祂自身「之外」。祂現在將他們視為現在實際存在的存有者,從事他們自己的實際工作,因為祂從亙古就已經將他們視為是將要存在的。祂對宇宙中當下發生的一切的知識,在邏輯上取決於祂從亙古就對宇宙所做的決定。
叁、人對上帝的知識
這一切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表達,即人的知識是神聖知識的類比。我們無法迴避就以下問題做出明確的決定:究竟是人的知識還是上帝的知識應該成為另一方的標準?其中一方必須是原創的,另一方必須是對原創的類比。一方必須是決定性的,另一方則是從屬的。羅馬天主教神學試圖在此同時事奉兩個主人。它也談到受造存有和人類知識是神聖存有和神聖知識的類比,但它並沒有真正認真對待這一點。在其哲學和護教學中,羅馬主義的推理方式是彷彿人可以自行決定知識的本質和可能性,而無需參照上帝。另一方面,它又提到奧祕是超越人類理解的。但作為更正教徒,我們應該堅定地選擇在知識的範疇內,以上帝為原創。
在我們探討對上帝的知識時,首先要指出的是,這種認識必須是真實的或客觀的。這再次涉及到我們對上帝的理解。上帝能夠分析性地、完全地認識自己,因此也必然能夠分析性地、完全地認識祂之外的一切事物。上帝當然必須對我們和整個宇宙有真實的知識。我們的存在和意義,我們的指稱(denotation)和內涵(connotation)都源自上帝。在我們存在之前,我們就已經得到了完整的詮釋了。上帝徹頭徹尾地認識我們;祂知道我們內心的所有想法。離開上帝的存在和意義,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存在和意義。這一切是從上帝通向我們的道路。但我們當然也可以藉著祂用來創造我們時所用的道路回到上帝那裏。如果我為了在某處建造一座城市而鋪設一條道路,那座城市的居民就可以藉著我建造的道路回到我這裏。當然,我們可以說,有人可能會摧毀那條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仍然存在,但城裏的居民無法回到我這裏。但這不能應用在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上。我們的存在不僅僅是由上帝而來,我們存在的意義也依賴於上帝。我們的意義只能透過歷史的進程才能實現。上帝創造人,是為了使人實現某個目的,就是榮耀上帝,從而使上帝達到祂自己的目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為上帝與人之間的道路已經切斷,這也意味著我們將不復存在,整個問題也就消失了。
因此,我們可以安全地得出結論:如果上帝就像我們所說的那樣,即一個作為自我完整之連貫系統而必然存在的存有者,而我們作為自我意識的存有者確實存在,那麼我們必定擁有關於祂的真知識。(我們現在不是在討論罪的問題。罪是一個倫理問題而非形而上學問題。我們對上帝在形而上學上的依賴,並沒有因為罪而被抹除。)當我們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時,我們在神學上表達的正是這一切。這使人像上帝,並確保人擁有對上帝的真知識。我們被祂所認識,因此我們認識祂,並且知道我們認識祂。上帝是光,因此我們有光。
堅持我們對上帝的知識必須是真實的(因為上帝就是祂所是的那樣)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堅持我們對上帝的知識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面的(comprehensive)。我們是上帝的受造物。我們現在無法全面地認識上帝,將來也無法指望全面地認識上帝。我們將來或許會比現在知道得更多。特別是當我們到了天堂,我們將比現在知道得更多,但我們仍然無法全面地知道。
因此,我們與上帝相似,所以我們的知識是真實的;而我們又與上帝不同,因此我們的知識永遠不可能是全面的。當我們說上帝對我們而言是奧祕時,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對祂的知識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真實的。當我們說上帝超越我們之上,或當我們說上帝是「絕對他者」時,我們並不是說上帝與我們之間不存在理性的關係。既然上帝按照祂的計劃創造了我們,也就是說,正如上帝按照祂絕對的理性創造了我們,那麼,我們與上帝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理性的關係。歸根究柢,基督教不是一種絕對的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而是一種絕對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事實上,我們可以將所有非基督教的知識論與基督教的知識論進行對比:基督教的知識論相信終極的理性主義,而所有其他的知識論體系都相信終極的非理性主義。
當我們說,身為基督徒我們相信終極的理性主義時,我們自然不是指我們作為人類擁有或可能在某個時候期望擁有對上帝的全面理性理解這樣的觀念。我們剛剛已經斷言了相反的情況。在這裏,每一種非基督教知識論都可以與基督教知識論區分開來,因為只有基督教知識論不以人類擁有全面知識為理想。原因在於,基督教認識論認為,全面知識只存在於上帝裏面。確實,如果任何地方存在著真知識,就必須存在著全面的知識,但這個全面知識無需、也不可能存在於我們裏面;它必須存在於上帝裏面。
肆、人對宇宙的知識
我們先前對人類認識上帝的論述,實際上決定了我們對人類認識宇宙的論述。我們現在所說的宇宙,是指整個受造世界,包括人自己及其所處的環境。
關於我們對上帝的知識與我們對宇宙的知識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提出的問題是:這兩者中哪一個優先?
人不可能不透過與其所處環境的關係來認識自己。知識的主體必須在與知識的客體的關係中、並藉由對比來認識自己。
這個關於人必須透過與其環境的關係來認識自己的主張,不僅僅是藉由觀察經驗而獲得的普遍性結論,而是基督教有神論的基石之一。這一點可以藉由再次參照我們關於上帝以及上帝與受造宇宙之關係的觀念來理解。人的存在源於上帝的存在。人的環境先於人而存在。上帝是人最終的環境,而這個環境完全詮釋了要認識自己的人。
換句話說,人的環境不是非位格的。此外,它也不僅僅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是位格的:即與他自己的出現同時,也有其他有限的位格,他在與這些位格的關係中認識自己為一個位格。在有限位格與其他有限位格以及其他有限但非位格事物的這種關係背後,是上帝的絕對位格性(absolute personality)。在人是否需要其他有限位格或需要有限的非位格環境這個問題背後,是人的直接環境之環境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man’s immediate environment)。上帝是人的終極環境,而這個終極環境控制著人的整個直接環境以及人自己。人的整個直接環境以及人自己,都已經被上帝所詮釋。甚至整個宇宙的指稱(denotation)都因上帝的內涵(connotation)或計劃而存在。因此,我們藉由回答邏輯優先性(logical priority)的問題,回答了關於現世優先性(temporal priority)的問題。因為人對上帝的認識在邏輯上比人對宇宙的知識更為根本,所以我們不必在意時間優先性的問題。即使在我們的心理經驗中,我們在有意識地談論上帝之前,就已經認識了自己和我們周圍的宇宙,但如果我們真正認識任何其他事物,那麼我們就一直都認識上帝。
我們不斷強調,上帝的概念是基督徒所信之一切事物的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上帝按照祂所是的方式必然地存在。正因如此,除非我們認識上帝,否則我們就無法在任何真正的意義上認識自己。祂是我們最終極的、因此是絕對不可或缺的環境。正因如此,如果我們認識祂,我們就能真實地(雖然不是全面地)認識祂。
由此可見,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真實的,雖然不是全面的。
除非我們既將知識的客體與上帝的關係,也將知識主體與上帝的關係都納入考量,否則我們關於宇宙知識之客觀性的論證就永遠無法完整且令人滿意。如果我們拒絕引入關於實在本質的形而上學問題,我們或許會無止境地爭論心理學的問題而一無所獲。如果基督教關於創造的立場,也就是說,關於人類知識之主體和客體起源的觀念是正確的,那麼客觀知識就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客體世界受造是為了讓知識的主體,也就是人,在上帝之下對其進行詮釋。如果沒有人為了上帝的榮耀而詮釋宇宙,整個世界就會毫無意義。因此,主體和客體是相互契合的。另一方面,如果基督教關於上帝創造的理論是錯誤的,那麼我們認為就不可能有對任何事物的客觀知識。在那種情況下,這個宇宙中的萬物彼此都是不相干的,彼此之間也無法進行富有成果的交流。我們相信,就這個宇宙的萬物而言,這就是關於知識客觀性問題的簡單抉擇。
當我們談到人類知識的客觀性時,一個常常令人困惑的問題是:人類對世界的知識是否必須是全面的才能被認為是真實的?有時有人會說,雖然我們不能指望獲得對上帝的全面知識,但我們或許最終(即使不是現在)能夠獲得關於宇宙萬物的全面知識。然而,我們相信,正是因為我們不能指望獲得對上帝的全面知識,所以我們也不能指望獲得關於世上萬物的全面知識。這並不是說世上萬物如同上帝那樣是無限的,因此無法被完全理解;因為使我們不可能全面理解受造宇宙中的事物的,並不是事物本身的無限性,而是再一次地,上帝的無限性。其原因不難理解。這個宇宙中的萬事萬物必須在與上帝的關係中被詮釋。如果知識的客體雖然與人類心智建立了關係,卻沒有與神聖心智建立關係,它就沒有被真實地詮釋。上帝是詮釋的終極範疇。我們現在無法完全理解上帝對受造物的計劃,所以我們也無法完全理解萬物。
由此可見,我們對宇宙的知識必須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受造物,祂造了我們,也造了宇宙。同樣,我們對宇宙的知識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因為我們對上帝的知識不可能是全面的。
這裏必須談一談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問題。2 人們不難推知,作為基督徒,我們所說的二律背反究竟指什麼。它們涉及這樣一個事實:人類的知識永遠不可能是完全全面的知識。每一次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action),都包含一個指向上帝的參照點。既然上帝對我們而言不是可完全參透的,我們在所有知識中必然會遇到看似矛盾的情況。我們的知識是類比性的,因此必然帶有悖論的色彩。我們說,如果要有任何真知識,上帝裏面就必須有一個絕對的知識系統。因此我們堅持認為,萬物都必須與上帝的那個絕對系統相關聯。然而我們自己卻無法完全理解那個體系。
為了說明我們在這裏的意思,我們可以舉一個基督教詮釋事物的突出悖論為例,即上帝的旨意與我們的禱告之間的關係。直截了當地說:一方面,我們說禱告能改變事物;另一方面,我們說萬事都按照上帝的計劃發生,而上帝的計劃卻是永恆不變的。
我們在這裏所關注的是要指出,就其本質而言,人類知識中必然存在這樣的悖論或看似矛盾之處。上帝作為自我完整的存有,獨立於我們而存在;祂是完全榮耀的。然而祂創造了宇宙,使宇宙可以榮耀祂。這一點是每個悖論或二律背反的根基。就其本質而言,我們在存在之前就已被完全詮釋了;上帝的普世計劃無需由歷史殊相來補充,也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補充。歷史事物無法產生任何全新的事物。這一點我們很清楚。上帝既然是祂所是的,那麼,祂的旨意就必然是作為有限的一與多背後不可或缺的,且是自足的(self-complete)統一體。對此,唯一的替代說法是歷史產生了全新的事物,而這將放棄基督教有神論的基本理念,即上帝以及祂創造宇宙並掌管宇宙的理念。另一方面,歷史必然具有真正的意義。否則上帝為何要創造它?禱告必然得到應允,否則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宇宙必然會真正榮耀上帝;那是它存在的目的。所以,一方面我們似乎提著一個裝滿水的水桶,另一方面,我們似乎還在往這個我們聲稱已經裝滿的水桶裏加水。
看來在人類知識中似乎必然存在矛盾。對此我們現在必須補充說,那裏似乎存在的矛盾,就事情的本質而言,只能是表面上的矛盾。如果我們說我們的知識中存在真正的矛盾,我們就會再次否認基督教有神論的基本概念,即上帝裏面自我完整之普遍性的概念。那樣我們就不僅是在說我們的思想中沒有完全的連貫性,而且也在說上帝的思想中沒有完全的連貫性。而這等同於說我們的思想中根本沒有連貫性或真理。如果我們說悖論或二律背反的觀念是真正矛盾的觀念,我們就摧毀了所有人類和神聖的知識;如果我們說悖論或二律背反的觀念是表面矛盾的觀念,我們就保存了上帝的知識,並且也保存了我們自己的知識。
我們必須在這裏再次強調,在護教論證中,對不同神學派別之間的差異視而不見是多麼不可能。這一事實在這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突出地顯明出來。亞米念主義並沒有忠於其自身對創造的信念。既然信奉創造,它就必須委身於我們所勾勒的關於上帝和上帝旨意的那種觀點,以及關於人與該旨意之關係的觀點。然而,它卻背離了所有這些原則,執意主張歷史進程確實能產生絕對的新事物。正因因此,它不得不將上帝的旨意與人的活動之間的關係視為真實的矛盾關係。為了避免這種「矛盾」,它乾脆拋棄了「上帝的旨意掌管萬有」這個理念。藉此,它實際上企圖摧毀神聖知識和人類知識,並藉此摧毀了它竭力維護的歷史意義本身。如果人們可以隨他們所願的拒絕救恩,上帝就無法回應我們為人們得救所獻上的禱告。
伍、罪及其咒詛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本章中關於人的知識的論述,還沒有將罪納入考量。我們只談到了上帝起初完美地創造人類時的正常情況。現在我們必須探究,當罪進入人的內心時,這種知識的狀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們知道,罪是人企圖與上帝斷絕關係的一種嘗試。但這種與上帝斷絕關係的情況,就其本質而言,不可能是形而上學的;如果是的話,人自己就會被毀滅,上帝對人的旨意也會落空。因此,罪是與上帝在倫理層面而非形而上學層面斷絕關係。罪是受造物對上帝的敵意和悖逆,但不是從受造身份中脫逃。
然而,當我們說罪是倫理性的時候,我們並不是說罪只涉及人的意志而不涉及他的理智。罪涉及人的位格的每個層面。人在上帝所設定的每一種關係中的所有反應都是倫理性的,而不僅僅是理智性的;理智本身就具有倫理性。
那麼,就知識問題而言,人類悖逆上帝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人類企圖在不以上帝為參照點的情況下詮釋他所接觸到的一切事物。他未來所有詮釋的前提是宇宙內部關係的自足性。這並不意味著人會立即公開否認上帝的存在。也不意味著人始終會、且處處會否認上帝在某種意義上是超越的。他始終否認的,至少就言外之意來說,是上帝是自足的(self-sufficient),或是自我完善的(self-complete)。充其量他會承認上帝與人類有關。他可能會說我們需要上帝來詮釋人類;但他同時會說,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也需要人類來詮釋上帝。他可能會說,現世性的事物若不參照永恆就無法被詮釋;但他同時會說,永恆若不參照現世性的事物也無法被詮釋。他可能會說,我們需要上帝,才能在我們的經驗中獲得統一性;但他同時會說,上帝需要歷史上的「多」(the historical many),才能將多樣性納入祂的經驗中。所有這些相關性形式,歸根究柢都等同於說有限的範疇是自足的。因此,我們可以在所有非基督教哲學的知識概念與基督教觀點之間作出一個非常簡單而全面的對比。聖經說,有些人敬拜並事奉造物主;他們就是基督徒。而其他所有人敬拜並事奉的是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
基督教有神論認為思想有兩個層次:絕對的和衍生的。基督教有神論認為詮釋者也有兩個層次:作出絕對詮釋的上帝,以及必須重新詮釋上帝之詮釋的人。基督教有神論認為,人類的思想因此是上帝思想的類比。與此相反,非基督教思想實際上主張,絕對思想與衍生思想之間的區別必須被抹去。誠然,上帝的思想可能比我們的更全面,但若沒有我們的思想,上帝的思想就不是自我完整的。這意味著,正如一切存有都被視為同等終極,因此,如今所有思想也被視為同等終極。只有一個層次的詮釋者;就算上帝進入這個圖景,也不過是作為人的合作者而已。我們不是跟隨上帝,按照祂的思想來思考,而是與上帝一起思考出從未被上帝或人思考過的思想。非基督教哲學主張,人類的思想是單義的(univocal),而非類比的(analogical)。
因此,基督教的類比思想概念和非基督教的單義思想概念,如同對立的兩極那樣,是相互對峙的。
非基督教思想堅持受造宇宙的終極性。因此它堅持人類心智本身的終極性,並因此必然否定類比思維的必要性。它既堅持人類心智的正常性(normalcy),也堅持其終極性(ultimacy)。它堅持人類心智的正常性,正如它堅持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的正常性。
當然,這種關於人類心智正常性的概念並不代表人類心智永遠不會犯錯。它僅僅意味著,人們認為犯錯是自然而然的,是可預期的,與罪無關。
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非有神論的思維尚未充分意識到其自身思想的含義,它就必然會將絕對全面知識的理想設定為目標。然而,它會堅持認為,人無需擁有任何全面普遍概念(comprehensive universal)也能生存。只要非有神論思維仍然認為人類需要擁有一個絕對普遍的概念,它自然就必須承擔起尋找這個普遍概念的任務,因為上帝已被排除在外。然後,當人類似乎永遠不可能找到一個普遍概念時——因為時間的特殊性按照定義總是先於任何由時間產生的普遍概念——人類便會說,無論如何,除了作為一個限制性的概念之外,他都不需要任何絕對普遍的概念。
在此或許有必要指出,在整個情況下,我們因此必須處理三種類型的意識。
首先是亞當的意識。當人起初受造時,他是完美的。他承認自己是受造物;他實際上是正常的。他只想成為上帝的詮釋的重新詮釋者。他樂於接受上帝在他內心和周遭環境顯明的啟示;他會重構這個啟示。他處在一種接受性地重構(receptively reconstructive)的狀態。因此,他在經驗中擁有真實的、儘管非全面的統一。
其次,我們來談談墮落的或未重生的意識。它建立在非有神論的假設之上。它實際上否認了其受造身份(creaturehood)。它自詡是正常的。它不願接受上帝的詮釋,而是想要在不以上帝為參照的情況下,創造自己的詮釋。它不會重構上帝的詮釋,只會建構自己的詮釋。它企圖進行創造性地構造,因此試圖去做不可能的事,結果卻是自我挫敗,其所有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非有神論思想中不存在統一性,也永遠不會有統一性;它已經切斷了與唯一存在的統一源頭的聯繫。然而,既然它無法在形而上學上切斷與上帝的聯繫,並且既然上帝為了實現祂的救贖計劃,那麼,關於上帝和宇宙的知識的遺跡(rudera)或火花(scintillae)就仍然留存在人裏面。正如保羅在羅馬書中告訴我們的,非基督徒在某種程度上是知道的。因此,即使在那些倫理上完全邪惡的人身上,也存在著相對的善。他們在經驗中所擁有的統一是一種如影子般的統一,一種防止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徹底瓦解的統一。此後,徹底瓦解終將到來,但即便如此,這種崩解也只能是倫理層面的,而非形而上學層面的;即使在地獄中,也必然存在某種王國或虛假的統一。
第三種是重生的意識。這種重生的意識在原則上已經恢復到亞當意識的狀態。它重新承認人是上帝的受造物,並且已經墮入罪中。它承認自己已被恩典拯救的事實。因此,它渴望回到接受性地重構的狀態。它想要根據永恆的一與多來詮釋現實。因此,在它的經驗,確實中存在統一性,儘管不是全面的統一。
然而,這種重生的意識只是在原則上得到了恢復。由於罪的殘餘仍然留在人裏面,即使在重生之後,它也無法完全實現自己的原則。因此,即使在原則上絕對良善的人,其內心也存在著相對的惡。這種絕對良善中的相對邪惡,對基督徒闡述有神論立場的一致性方面,產生了極大的不利影響。而這種不一致體現在言語和行為中,既體現在對基督教理性論證的妥協性表達上,也體現在基督徒所過的非基督徒的生活中。因此,非基督徒往往無法全面了解擺在他們面前的基督教立場。
所有這些都使得護教論證的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只有清楚地認識到三種類型的意識,認識到未重生之人的意識本身完全無法接受基督教真理,認識到必須始終如一地闡述基督教立場,並堅定地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幫助我們與人進行富有成效的辯論。
註腳:
1. 一份未發表的課程大綱。
2. 參《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