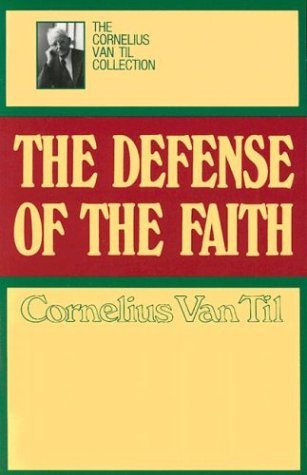
《信仰的護衛》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作者: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
誠之譯自: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Philadelphia, 1955), 51–66.
第四章 基督教行為論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Behavior
在簡要闡述了基督教的存有觀和基督教知識觀之後,現在必須簡要說明基督教的人類行動或行為觀。
在闡述基督教倫理觀時,我們從改革宗各信條中採用這個簡單的陳述,即善行必須是為榮耀神而行。
因此,我們所說的人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是指身為得贖的受造物,若要榮耀上帝就必須追求的目標。他要在地上具體地透過努力建立上帝的國度來實現這一點。
其次,人不能自己設定標準或準則來努力實現上帝的國度。他的標準必須是聖經中所啓示的上帝的旨意。
第三,作為罪人,人沒有任何能力來為實現上帝的國度而努力。沒有信心就不能討上帝的喜悅。而信心來自上帝,藉著聖靈的重生而來。
這種信條式的倫理體系非常簡單。它使我們能夠在倫理學文獻的迷宮中找到方向。所有作家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人的 (a) 至善(summum bonum)、(b) 準則,與 (c) 動機。
壹、倫理學與基督教知識論
為了處理基督教的至善(summum bonum)、基督教標準和基督教動機,我們可以首先說明整個基督教倫理學如何直接關聯到基督教知識觀。我引用的是《基督教倫理學》講義中的內容。
作為絕對位格的上帝,是人在其存在各個方面的終極解釋範疇。就本質而言,上帝的每個屬性首先會反映在上帝的其他每個屬性裏。三位一體的三個位格之間的關係將是相互的且完整全面的(mutual and complete exhaustiveness)。因此,三位一體中的任何一個位格,在其存有上,與神格(Godhead=神性本體)以外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說是互相依存的(correlative)。如此,如果說人是受造的,那麼他在其存在的各個方面,都必須絕對依賴於他與上帝的關係才會有意義。如果這是真的,就意味著善之所以對人為善,是因為它被上帝設定為對人為善。這通常表達為:善之所以為善是因為上帝說它是善。這與非基督教思想形成對比,後者認為善本身是存在的,上帝所追求的,是本身就是善的東西。我們不能人為地將上帝的旨意與上帝的本性分開。上帝的本性與旨意才是最終極的善。然而,既然上帝的本性是位格性的,我們就不能說善本身就是存在的。
作為絕對位格的上帝,是人在其存在各個方面的終極解釋範疇。
a. 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
以上述考量為背景,我們可以思考人最初出現在地上的情景。從邏輯上可以推斷出,人出現在地上時,是神格完美但有限的複製品(a perfect though finite replica)。人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道德方面,其原初的完滿(original perfection)已經隱含在上帝的概念裏,而上帝的概念是整個基督教思想結構的基石。
既然在上帝裏面不可能有任何邪惡,那麼認為祂會創造邪惡的人就是完全無法想像的。這不僅因為我們厭惡將這種行為歸咎於上帝,更是因為這樣做會與祂的存有相矛盾。因此,我們認為人最初出現時具有完美的道德意識。創世記的敘事正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除非我們強調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在其原初的完美狀態下,人的道德意識也是衍生的,而非判斷何為善的終極信息來源,否則基督教倫理學與非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差異在這一點上就沒有被完全澄清。人本質上是有限的。因此,他的道德意識也是有限的,因而必須依靠啓示而存活。人的道德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都必須處於一種接受性地重構的(receptively reconstructive)狀態。
人的道德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都必須處於一種接受性地重構的(receptively reconstructive)狀態。
這就是基督教認識論與非基督教認識論之間最基本和根本的區別,就其直接關係到倫理學問題而言:在非基督教思想中,人的道德活動被認為是創造性地建構的,而在基督教思想中,人的道德活動被認為是接受性地重構的。根據非基督教思想,不存在一個絕對道德位格,人無需對之負責,也無需從那裏獲得善的觀念;而根據基督教思想,上帝是那無限道德位格,祂向人啓示了道德的真實本質。
然而,我們必須將上帝對人的這種啓示視為最初既是內在的也是外在的。人在自己的構造中、在自己的道德本性中,都發現對善的理解和熱愛。他自己的本性就是上帝旨意的啓示。但是,儘管人的本性如此啓示了上帝的旨意,但即便在樂園中,人的本性也從未意味著要單獨運作。它總是要由上帝旨意的超自然、外在和積極的表達來補充,彼此相互依存。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在人的道德本性與倫理學問題的關係上的看法,存在著多麼根本的差異。
b. 罪及其咒詛
上述一般對立的觀點中必須包含的第二個差異點,涉及罪對人的道德意識的影響。我們在此無法對所有與此問題相關的聖經素材進行全面考察。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主要觀點已經夠清楚了。正如罪蒙蔽了人的理智,它也敗壞了人的意志。這通常被稱為人心的剛硬。保羅說,屬血氣的人與上帝為敵。屬血氣的人無法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甚至無法分辨何為善。罪人敬拜受造之物,而非敬拜造物主。他已將所有道德標準顛倒過來。
這個關於人全然敗壞的教義清楚表明,人如今的道德意識無法提供關於何為理想之善、何為善的標準,或何為追求善的意志的真實本質的信息來源。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人們必須在基督教立場和非基督教立場之間做出選擇。
正是這一點尤其使得基督徒必須毫不妥協、毫不讓步地堅持:一切道德問題都必須在聖經,且唯獨在聖經的光照下來回答。聖經作為外在啓示,因著人的罪而成為必要。除非在聖經的光照下,否則活著的人都根本無法說明他應該說明的道德問題,或正確地提問他應該提問的道德問題。人憑自己無法真正面對道德問題,更不用說回答它了。
因此,人類今天的道德意識是 (a) 有限的,和 (b) 有罪的。如果它只是有限而非有罪,我們還可以向人的道德意識尋求信息。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謹記,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不是因為道德意識能夠僅憑自己的能力正確地提出或回答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它本身的活動會與上帝保持富有成效的接觸,所有的問題和答案最終都必須來自上帝。
誠然,未重生之人的意識無法完全壓制上帝透過其自身構造向它發出的各項要求。因此,它不由自主地仍可聽見上帝透過它所發出的旨意。因此,屬血氣的人會為自己的倫理行動開脫或自責。但就目前所討論的主要論點而言,這一點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只要人受到上帝普遍恩典的約束,因而沒有徹底放縱自己的罪惡原則,屬血氣的人就會把自己的道德意識視為道德行動的終極標準。
未重生之人的意識無法完全壓制上帝透過其自身構造向它發出的各項要求。因此,它不由自主地仍可聽見上帝透過它所發出的旨意。
c. 重生的意識
那麼,重生的道德意識又如何呢?首先,重生的意識在原則上再次恢復到其原來的位置。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求助於它,因為我們原本就可以向它尋求答案。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它提供了基督教倫理學與非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接觸點。身為基督徒,我們並不主張人的道德意識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作為參照點。然然,人的道德意識必須重生才能作為參照點。此外,重生的意識仍然是有限的。它必須像起初那樣,仍然依靠啓示而活。它永遠不能成為終極的資訊局(information bureau)。最後,重生的道德意識只是在原則上發生了改變,因此常常會犯錯。因此,它必須不斷努力用聖經來檢驗自己。不僅如此,重生的意識本身不會捏造任何道德問題的答案。它接受答案,並重新思考和處理答案。如果將這種接受——就其所暗示的心智活動而言——稱為道德意識的功能,我們就可以將其視為信息的來源。不斷從聖經中汲取養分、得到重生的道德意識,就好比一位全權代表,相當清楚自己的權威想要的是什麼。
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關於人的道德意識的兩種理解。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a) 曾經存在著一種完美的道德意識,它可以作為道德問題的直接信息來源,但只是作為就近的來源;(b) 如今有兩種類型的道德意識,就其按照各自原則運作而言,在任何倫理答案和任何倫理問題上都無法達成一致,即未重生的意識和重生的意識;(c) 未重生的意識否認、而重生的意識則確認,由於人的罪,任何人的道德判斷都必須以聖經來察驗。
未重生的意識否認、而重生的意識則確認,由於人的罪,任何人的道德判斷都必須以聖經來察驗。
d. 羅馬天主教
在本章討論的問題上,羅馬天主教採取了介於基督教和異教之間的中間立場(a position half way)。在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所闡述的人類意識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亞里士多德的形質論(form-matter scheme)發展出來的。結果,相對於上帝的意識,人類意識被賦予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性。這在知識場域(field)是如此,在倫理學場域同樣如此。
在倫理學場域裏,這意味著即使在樂園中、在墮落之前,人也不被認為在對上帝的態度上是處在一種接受性地建構的狀態。為了維護人的自主性——或者如托馬斯所認為的,維護人作為自我意識和負責任的存有的人的身份(manhood)本身——人必須(至少從某個角度來看)完全獨立於上帝的旨意。這隱含在所謂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中。如果人的所有行動的終極和最終參照點完全是上帝及其旨意,托馬斯就無法認為人是負責任和自由的。因此,在羅馬主義中沒有真正符合聖經的權威觀念。
由此可見,羅馬對墮落之人的道德意識抱持著過高的期望。根據托馬斯,墮落的人與樂園中的亞當並無太大不同。他說,雖然罪人比亞當需要更多恩典來完成更多的事,但他對恩典的需求並不比亞當更多。1 托馬斯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說到:「因此,在完美本性的狀態下,人只因一個理由需要一種白白賜下的力量,一種額外加在自然力量之上的能力,那就是為了行善並渴望超自然的善。但在本性敗壞的狀態下,人則因兩個理由需要這樣的恩典:一是為了得醫治,二是為了履行那些屬於超自然德行、且具有功德的行為。除此之外,無論處於哪一種狀態,人都需要上帝的幫助,才能被感動而行善。」2 無論如何,對托馬斯來說,人的倫理問題既是有限性(finitude)的問題,也是倫理順服的問題。人天生是有限的。因此自然傾向於作惡。即使他不是罪人,他作為受造物,仍然需要恩典。因此,上帝實際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虧欠人恩典。當人沒有善用賦予他的恩典以完全遠離罪惡時,他也並非變得全然敗壞。因為無論如何,他自由意志的行為本身,就自然地使他陷入嚴重的危險之中。因此,墮落的人只是部分有罪,也只是部分應受責備。他還保留著人在樂園中所擁有的大致相同的倫理能力。因為倫理能力實際上被認為隱含在形而上學的能力或自由意志之中。
由此可進一步推論,即使是重生的意識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順服於聖經。托馬斯無法公正對待聖保羅的立場,即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托馬斯對「四樞德」(cardinal virtues;譯按:指智德、義德、勇德、節德)及其與神學美德關係的整個討論證明了這一點。他在它們之間做出了明確區分。「神學美德的對象是上帝自己,祂是萬物的最終目的,超越我們理性的知識。另一方面,智性美德和道德美德的對象是人類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因此,神學美德在種類上並不同於道德美德和智性美德。」3 那麼,對於那些被認為無需超自然啓示,就可以憑理性認識的事物,基督徒的行為和應當採取的行動,其動機實際上與非基督徒相同。基督徒在生活的自然關係中以美德行事,並不需要信心。或者說,如果神學美德確實對基督徒的日常活動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偶然的/附帶的(accidental)、輔助性的/次要的(subsidiary)。
綜上所述,很明顯,羅馬主義無法要求其信徒徹底地將其道德意識順服於聖經。因此,羅馬也無法徹底地挑戰非基督教的立場。
羅馬主義無法要求其信徒徹底地將其道德意識順服於聖經。因此,羅馬也無法徹底地挑戰非基督教的立場。
e. 福音派
福音派更正教徒經常持有與羅馬主義類似的立場。作為近期的例證,我們提到魯益士(C. S. Lewis)的情況。
與羅馬主義一樣,魯益士首先混淆了形而上學和倫理學的概念。在他的書《超越位格》(Beyond Personality)中,他討論了神聖三位一體的本質。為了說明三位一體教義的實際意義,他說:「這整個舞蹈、戲劇或這三位格生命的模式,都將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上演;或者(反過來說)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進入那個模式,在那場舞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4 基督教的目的就是將人的生命(Bios),或自然生命提升到未受造的生命(Zoe)裏。5 在道成肉身中,我們已經看到這是如何實現的,在祂裏面,「有一個人,從祂母親那裏獲得的受造生命,完全而完美地轉化為上帝所生的生命。」然後他補充說:「那麼,祂對人類全體究竟帶來了什麼改變呢?那就是:成為上帝的兒子,從受造之物轉化為上帝所生的,從短暫的生物生命過渡到永恆的『屬靈』生命,這一切都由祂替我們完成了。」6
所有這些在含義上都與阿奎那的立場類似,後者強調這樣的觀念,即人乃是透過恩典參與神性。
勿庸置疑,倫理問題不能以此為基礎作出公正的界定。或許,所有形式的非基督教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認為,人的有限性本身導致了他的倫理困境;而後者則認為,不是有限性本身,而是受造的人類對上帝的悖逆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魯益士未能清楚表明這一區別。魯益士沒有以嘹亮的聲音呼召人們回歸對聖經所顯明的上帝的順服。他要求人們「裝扮成基督」(dress up as Christ),以便當他們將基督理想置於面前,並看見自己距離實現這一理想有多遠時,基督——此時就在他們身邊——可以將他們「轉變成與祂自己相同的人」,並將「祂那種生命和思想,即祂的生命(Zoe)」,注入他們心中。7
所有形式的非基督教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認為,人的有限性本身導致了他的倫理困境;而後者則認為,不是有限性本身,而是受造的人類對上帝的悖逆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
魯益士認為,「恢復對罪的古老理解,對基督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8 10那麼,他為什麼又鼓勵人們認為,人類陷入到一種形而上學張力之中,是連上帝也無法掌控的呢?魯益士說,人們不太可能恢復對罪的古老理解,因為他們沒有洞察道德行為背後的動機。9 但是,如果鼓勵人們認為,即使沒有聖經的光照,以及聖靈重生大能的情況下,他們至少在自然領域可以做正確的事,那麼如何能挑戰人們反躬自省,並發現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呢?即使他沒有信心,人們真的能按照應有的方式實踐智德(prudence)、節德(temperance)、義德(justice)和勇德(fortitude)的「四樞德」,嗎?任何更正教徒都不應承認這種可能性。
魯益士在倫理學、文學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尋求客觀標準。但他認為客觀性在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他談到一種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共有的普遍客觀性,並論證說,這種客觀性幾乎完全是在現代社會才被人拋棄的。談到這種普遍客觀性,他說:「這個概念,無論其形式是柏拉圖式的、亞里士多德式的、斯多葛式的、基督教式的,還是東方的,為了簡潔起見,我以後都簡稱其為『道』(the Tao)。我引用的一些關於它的描述,或許在你們許多人看來只是古怪的甚至是神秘的。但它們的共同點在於,這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那就是客觀價值的教義,即相信某些態度對於宇宙的本質和我們的本質而言,是真正正確的,而另一些則是真正錯誤的。」10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普遍客觀性,僅僅在形式上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共有的。說存在或必須存在一種客觀標準,並不等於說那個標準是什麼。而「這是什麼」才是至關重要的。誠然,那些信奉在某處有某種凌駕於人之上的事物的非基督徒,比那些什麼都不信的非基督徒來得好,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根本問題上,非基督教客觀主義者與非基督教主觀主義者都是同樣主觀的。最終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在順服上帝的人和取悅自己的人之間的選擇。只有那些藉著基督信靠上帝的人,才會努力順服上帝;只有他們才擁有真正的倫理原則。魯益士的言論傳遍世界,這固然令人欣慰,但他在呼召人們回歸福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托馬斯·阿奎那的方法,這實在令人遺憾。「聖魯益士的福音」與屬血氣之人的觀念妥協太多,以至於在我們這個時代無法構成明確的挑戰。
貳、倫理學與基督教實在論
正如上帝是絕對理性,上帝也是絕對意志。這話的意思主要不是指上帝必須成為良善,而是說從亙古到永遠,祂一直就是良善的。在上帝裏面不存在主動與被動的問題。在上帝裏面才會有永恆的成就。上帝最終且終極地是自我決定的。上帝最終且絕對地是必然的,因此也是絕對自由的。
應特別注意的是,基督徒提出這個關於上帝的概念,不是作為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的概念。從非有神論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上帝必然顯得像所有難題的垃圾堆積場。我們暫且擱置這一反對意見,是為了要大家注意,基督教觀點與非基督教觀點在倫理學領域中的所有分歧,最終都必須追溯到他們不同的上帝觀。基督徒認為,上帝的概念是所有人類活動的必要前提。而非基督教思想則認為,基督教的上帝觀則是扼殺了所有倫理活動。所有非基督教倫理學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基督徒所信奉的上帝並不存在。而非基督教思想理所當然地認為上帝的意志和人的意志一樣,都受到環境的左右。非基督教倫理學假設一種終極的行動主義(activism)。對它來說,上帝必須成為良善。無論對上帝還是對人來說,品格都是透過某種過程所獲得的成就。人們認為上帝既是被決定的(determinated),也是已決定的(determinated),同時有是決定他者的(determinative)。
非有神論的出發點是假設一種最終不確定的實在。因此,對它來說,所有確定的存在、所有的位格性都是衍生的。
唯心主義者(idealist)可能會反駁說,在柏拉圖的永恆之善(the eternally Good)中,以及在現代唯心主義的「絕對」理念(idea of the Absolute)中,都沒有提到成就。會有人說,在那些概念中,你擁有的是絕對的自我決定的經驗。對此,我們只想指出,柏拉圖的上帝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終極存在。至善而非上帝,才是柏拉圖最終極的概念。他的上帝,即使具有位格而化的特徵,也只是比喻性的(metaphorical),而且無論如何,都依賴於一個比自己更終極的環境。在柏拉圖哲學中,偶然性(element of Chance)才是絕對終極的。正是偶然性的這種終極性,要麼使確定的善成為一種成就,要麼使善脫離其環境,從而摧毀其價值。
至於現代唯心主義的絕對概念,應當注意的是,它是明確而長期努力尋找一種絕對的自我決定經驗的概念(an absolutely self-determinative Experience)所造成的結果。就我們看來,唯心主義者基本上確信,除非可以預設一種絕對自我決定的經驗,否則所有人類經驗——尤其是倫理經驗——都將毫無意義。現代唯心主義明確試圖將柏拉圖的善與其環境建立起一種富有成效的關係。然而,它並沒有克服柏拉圖倫理學固有的難題。它最終得到了一個被決定的上帝,而非自我決定的上帝。它理所當然地認為時空宇宙是終極存在的一部分或層面。有了這一假設,它使時間與永恆一樣終極,並使上帝依賴於可能從時空母體中產生的任何東西。
如此,區分基督教倫理學與非基督教倫理學的基本分歧,就是接受或否認上帝最終自我決定的意志。身為基督徒,我們認為,如果不是因為上帝的絕對意志是存在的,否則人類確定性的經驗就無法朝著任何目的努力,無法按照任何計劃進行,甚至根本無法啓動。
因此,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堅定認為上帝的絕對意志是人類意志的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對許多人而言,乍看之下似乎是人類責任最大障礙的東西——也就是絕對主權之上帝的概念——恰恰成為其可能性的根基。
然而,為了避免誤解,我們應該區分絕對位格主義環境(absolutely personalist environment)的概念與哲學上的決定論(determinism)。人們經常過於草率地將連貫一致的基督教與哲學上的必然論(necessitarianism)視為等同,這種情況太常見了。然而它們卻有天壤之別。哲學上的必然論代表一種終極的非位格主義(impersonalism);而連貫一致的基督教則代表終極的位格主義。這對於人的意志活動本身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可以簡要考察。
叁、上帝的國作為人的至善
a. 非基督教的至善
非基督教倫理學作家為自己設定的人類行為理想是什麼?所有非基督教理論與基督教至善理論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所有非基督教倫理學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如今的存在是正常的。我們關於人的原初狀態的觀念,在他們看來不僅是一個可悲的幻想,而且是一種不可原諒的傲慢。人們樂於閱讀夢想家所夢想的烏托邦;他們甚至樂於將創世記的故事納入他們閒暇時間的輕鬆讀物清單,但人們反抗被告知他們的倫理理想必須由亞當的倫理理想來評判。11
對原初完美倫理理想的這種反對,其真正含義無非是對永生上帝的仇恨。如果上帝確實作為人的創造主存在,那麼正如我們所見,邪惡不可能是現世宇宙所固有的。如果上帝存在,那麼,罪惡必定是人自己蓄意犯罪的行為所帶來的。因此,如今的存在就不是正常的,而是不正常的。相應地,堅持認為現如今的存在是正常的,就等於否認人類對罪惡的責任,而這反過來又使上帝要對罪負責,而這便意味著根本不存在絕對的上帝。
除了假設人的道德意識是正常的之外,非基督教觀點還假設它是非受造的或終極的。即使當絕對唯心主義者談到上帝是絕對者時,這位上帝也不是人的創造者。要更好地觀察到真正的基督教自我發展理論與唯心主義自我發展理論之間的差異,我們就必須明白,唯心主義的觀念是基於非基督教對「有待實現的自我」這個概念。在這種觀念中,「自我」不被視為是上帝的受造物,而是理性的一個面向,它以某種方式存在於宇宙中,與其他同樣以某種方式存在於宇宙中的理性微粒並存。
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說得夠多了,足以闡明用來區分基督教與非基督教至善的主要對比。我們已經指出,非基督教倫理學各個學派之間的所有對比,如理性主義(intellectualistic)與意志主義(voluntaristic)之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自私與利他之間、幸福與良善之間、有用與美德之間的種種對比,都源於對上帝與人之間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假設(assumed correlativity)。這就假設了上帝與人相互依存的關係(correlativity)。這種對創造論的假設的否定(assumed denial),這種假設的惡的終極性,除了公平交換(give-and-take)、個體之間的「索賠與反索賠」之外,完全不允許有任何其他倫理理想;這些個人必須生活在一起,卻又必須以犧牲彼此為代價而生活。令人驚奇的是,從這樣的土壤中竟然萌發出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的崇高倫理學。這只能歸功於上帝的普遍恩典。
b. 聖經的至善
與這種以人為中心(人被假設為是正常的、而且是終極的)的非基督教的人類至善(summum bonum)觀相反的,是聖經的觀點。
1. 絕對理想(absolute ideal)得到了維護。《舊約》和《新約》作為一個整體,堅持認為上帝作為人的創造者和審判者,很自然地必須為人類的生活設定理想。無論是《舊約》或《新約》的倫理學都認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有能力完美地遵行上帝的旨意。這種對人的觀念包含在絕對理想的概念中。除了《舊約》和《新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關於人類原初完美狀態的觀念,這一事實本身又反過來證明了人被賦予了絕對理想。
即使在人類墮落之後,上帝仍然把絕對完美——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種族的——的理想擺在人面前,這是人不僅必須追求而且實際上必須實現的目標。
2. 然而,由於他身為罪人,他甚至無法朝著實現這一理想——即上帝的國度——邁出第一步,因為上帝的國被視為人的至善,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使命(Aufgabe)已經成為恩賜/禮物(Gabe),正如恩賜(Gabe)對人來說也是使命(Aufgabe)。
3. 第三,聖經中的至善要求徹底消除個人和社會中的罪與邪惡。在《舊約》時代,這一目標必須透過外在的方式達成,而在《新約》時代,這一目標則需要透過更屬靈或內在的方式來實現。但無論在哪個時代,目標都是一致的。
我們在消滅邪惡方面的任務,並不是在我們努力對抗我們所見到的一切罪惡時就結束了。我們還有進一步的義務,要盡可能地摧毀罪惡在這個世界上造成的後果。我們必須向所有人行善,特別是向信徒家裏的人。幫助減輕上帝的受造物所受的苦難,是我們的特權,也是我們的使命。
這就是至善的第三個面向。我們擁有一個絕對的倫理理想可以提供給世人。這個絕對理想是上帝的恩賜。這給了我們勇氣,讓我們著手從上帝的宇宙中根除邪惡。我們不能從上帝最初安置人的地方著手。我們必須花大量時間用在摧毀邪惡。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或許甚至看不到自己或周圍環境有多大進展。我們將不得不一手拿著水泥鏟子,一手拿著劍來建造。這在我們看來,或許只是一項試圖要把海水抽乾的無望任務。然而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是基督徒,這正是我們的倫理理想的樣子。我們知道,對非基督徒來說,他們的倫理理想無論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永遠無法實現。他們甚至不知道真正的倫理理想是什麼。至於我們自己的努力,我們知道,儘管我們可能要花費大量時間用來清除罪惡的水,但我們仍然在堅固的磐石上奠定我們橋樑的根基,我們正朝著我們的目標不斷前進。我們的勝利是確定的。魔鬼及其所有爪牙將被趕出上帝所造的宜居的宇宙。將會有一個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譯按:參彼後三13)。
4.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聖經倫理學的第四個特徵,即它是一種充滿盼望的倫理學。它意味著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確信中,即宇宙能夠、也並將在上帝所定的時間裏完全更新。它意味著盼望新天新地的到來。
這就是聖經的倫理理想。它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絕對理想,是其他任何倫理文獻都無法比擬的。這個倫理理想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而踏上通往這一倫理理想的能力也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正是這一點給了我們確據,這個理想毫無疑問必將實現。如此,這個倫理理想,正因為它是絕對的,就要求要消滅一切邪惡。因此,無論在《舊約》還是在《新約》中,消滅邪惡都是上帝子民使命的一部分。最後,由於這個倫理理想是一個絕對理想,並且要求徹底除滅邪惡,它的完全實現就只能在來世;聖經倫理學是一種充滿盼望的倫理學。
從這個描述來看,聖經的這一倫理理想是獨特的,應該是非常明顯的。沒有其他倫理理想哪怕是在最遙遠的程度上能與之相似。所有其他理想都設想一個相對的目標。它們都不認為這個理想是給人的禮物。它們都不要求徹底消滅邪惡。它們都不期待在來世充分實現其理想。《舊約》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像《新約》一樣獨特。它們在這些要點上完全一致。它們一起與所有其他倫理理想完全相反。
關於準則和動機方面,更全面地討論基督教倫理學與非基督教倫理學的差異,會使我們離題太遠。在這兩方面,改革宗信仰所秉持的基督教立場都圍繞著關於上帝、創造、墮落,以及藉著基督得蒙救贖的教義。基督徒以上帝啓示的旨意為標準。這個標準是絕對的。而非基督徒則以人類經驗為標準。同樣,基督徒藉著上帝賜給他信心的能力,遵循他的標準,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非基督徒,無論是實在論者、唯心主義者還是實用主義者,都努力憑自己的能力來實現其理想。
註腳
1.《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英國道明會神父譯,第4卷,第324頁。
2. 同上,第8卷,第327頁。
3. 同上,第7卷,第150頁。
4.《超越位格》(Beyond Personality),第27頁。
5. 同上,第28頁。
6. 同上,第1卷,第31頁。
7. 同上,第37頁。
8.《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第45頁。
9. 同上,第47頁。
10.《人的廢除》(The Abolition of Man),倫敦,1947年,第17頁。
11. 創世記的敘事,如果被視為歷史事實,再次成為基督教倫理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