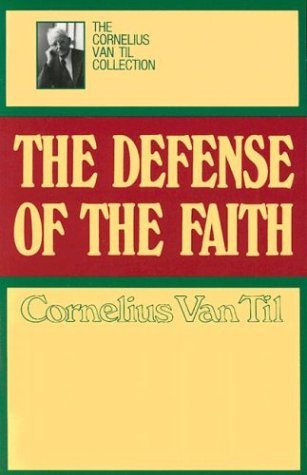
《信仰的護衛》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作者: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
誠之譯自: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Philadelphia, 1955), 67–95.
第五章 基督教護教學(接觸點)
Christian Apologetics (Point of Contact)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處理了改革宗基督徒信「什麼」(what)的問題。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們關注的是他應當如何(how)護衛並傳揚他所信的。
在本章中,主題將是接觸點(point of contact)的問題,而在下一章中將是方法的問題。
在這兩個問題上,改革宗神學家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這種分歧的本質將在討論過程中顯明出來。
當信徒向非信徒闡述基督教的人生觀時,可以在非信徒的心靈中找到什麼接觸點/切入點,從而引起他們的共鳴的呢?1
是否存在一個雙方都知道的領域,我們可以從這個起點出發,進而達到信徒知道但非信徒不知道的領域呢?是否存在一種認識這個「已知領域」的共同方法,只需將其應用到非信徒不知道的事物上,就能使他確信其存在及其真理呢?我們不能在一開始就假定這些問題必須以肯定的方式回答。因為認知者本身與他所認識的事物一樣都需要詮釋。人類心靈作為認知主體,會對其所獲得的知識做出貢獻。因此,除非信徒和非信徒對人性本身的看法達成一致,否則在他們之間找到共同的知識領域將是天方夜譚。但這種一致性並不存在。在他最近的著作《人論》(Essay on Man)中,恩斯特·卡西勒(Ernest Cassirer)追溯了哲學家們在歷代提出的各種人性理論。卡西勒斷言,我們現代的人性理論已經失去了其智識中心(intellectual center)。「相反,我們獲得了思想的完全無政府狀態。誠然,即使在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各種觀點和理論也存在巨大差異。但至少還存在著一個總體方向,一個參照框架,所有個別差異都可以歸屬其中。形而上學、神學、數學和生物學相繼承擔了關於人的問題的思考指引,並決定了研究路線。當這樣一個能夠指導所有個別努力的中心能力不復存在時,這個問題的真正危機就顯明出來了。這個問題的至高重要性在所有不同的知識和探究分支中仍然可以感受得到。但一個可以訴求的既定權威已經不復存在了。神學家、科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都從各自的觀點探討這個問題。要結合或統一所有這些特定的方面和視角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專門領域內也沒有普遍接受的科學原則。個人因素變得越來越普遍,而個別作者的氣質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人各有所好」(Trahit sua quemque voluptas);每個作者最終似乎都受到他自己對人類生活的概念和評價的引導。」2
卡西勒在此描繪的現代流行的人觀(anthropology)的混亂本身就足夠令人沮喪了。但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現代思想普遍持有的人的概念,不能被假定為與聖經所闡述的相同。因此,基督教護教者必須警覺到這樣一個事實:他必須把基督教信仰介紹給普通人,而這個普通人與他自己所認為的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一位好醫生不會根據病人對自己的診斷來開藥。病人可能認為他只需要一瓶藥,而醫生知道需要立即進行手術。
因此,基督教必須以光的面貌出現,這光可以叫人類經驗的事實,尤其是人性本身,顯現其真實面貌。基督教是人類生命和光明的源頭。
壹、羅馬天主教
強調剛才所提出的觀點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更正教徒發現有必要與羅馬天主教徒就基督教本身的性質進行辯論,他將同樣發現有必要與他就接觸點的問題進行辯論。更正教神學需要更正教護教學。
更正教與羅馬天主教在「接觸點」這個概念上的差異,自然必須以類似於我們陳述更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神學之間差異的方式來表述。有兩種陳述這種差異的方式。一種非常常見的方式是首先指出這兩種類型的神學所共有的教義領域,然後再列舉它們之間的差異。這就是華腓德在其名正言順的著名小册《救恩計劃》(The Plan of Salvation)中所採取的路線。華腓德說,在那些持守某種救恩計劃的人當中,有些人以自然主義(naturalist)路線思考這個計劃,而另一些人則以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t)路線思考這個計劃。相對於持自然主義觀點的伯拉糾主義者,「整個有組織的教會——希臘正教、羅馬天主教、拉丁教會,以及更正教的所有重要歷史形式,路德宗和改革宗,加爾文主義和亞米念主義——都一致、堅定和強調地見證救恩的超自然主義概念。」3
從這一點往下,華腓德接著將超自然主義者分為聖職主義者(sacerdotalist)和福音派。他們之間的爭議涉及「上帝拯救作為的直接性(immediacy)」。持聖職主義觀點的羅馬教會教導「恩典是透過且靠著教會的各種儀式(ministrations)來傳遞的,否則就無法傳遞。」另一方面,福音主義則「尋求保存它所認為的唯一一致的超自然主義,掃除靈魂與其上帝之間的每一個中介,使靈魂的救恩僅僅依賴於上帝,透過祂的直接恩典作用於靈魂。」(19頁)而更正教主義和福音主義是「重疊的coterminous=共享邊界),即使不是完全同義的稱謂。」(20頁)
在這一點上,華腓德繼續標示更正教內部的主要變化。在更正教徒或福音派中,有些人持守普世主義(universalistic)的救恩計劃概念,而另一些人則持守特殊主義(particularistic)的概念。「所有福音派都同意,拯救靈魂的所有能力都來自上帝,而這種拯救能力是直接作用於靈魂的。但他們對於上帝是否平等地、或至少是不加區別地對所有人施行這種拯救能力(無論他們是否實際得救),還是僅對特定的人,即那些實際得救的人施行,存在著分歧。」(22頁)當他再次標示普世主義福音派和特殊主義福音派之間的差異時,華腓德使用了這些話:「因此,區分普世主義者和特殊主義者的確切問題,正是上帝的拯救恩典(唯有身在其中才有救恩)是否真的會拯救人。」(24頁)
追隨華腓德進一步區分各種形式的特殊主義者與我們的目的無關。「重大意義的差異」(differences of large moment)(27頁)現在已經擺在我們面前了。華腓德為特殊主義或加爾文主義辯護。而使用福音派一詞來指稱非加爾文主義的更正教徒已成為慣例。
華腓德為特殊主義或加爾文主義辯護。而使用福音派一詞來指稱非加爾文主義的更正教徒已成為慣例。
現在令我們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儘管華腓德的出發點是共同點(common denominator)的觀點,但他每次標示出一個新的差異時,都不得不指出這是為了保持一致性的緣故。更正教徒之所以是更正教徒,是為了比羅馬天主教徒更一致地持守超自然主義。加爾文主義者之所以是特殊主義者,是為了比其他更正教徒更一致地持守福音派立場。根據華腓德的說法,加爾文主義者旨在持守一種「不受外來侵入元素染污」的立場。(21頁)因此,各種救恩概念「並非簡單地並列,作為對救恩計劃的不同理解,彼此對立。相反,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對一個原初錯誤的一系列漸進式修正,在體現救恩這一根本理念的過程中,越來越趨於一致。」(31頁)
由此看來,華腓德本人實際上提出了一種比他自己所採用的更好的方式,來表達羅馬主義與更正教主義之間,或普世主義與特殊主義更正教主義之間存在的差異。約翰·慕理(John Murray)教授指出了這種更好的方式,他說:「因此,更真實、更有效、從各方面來說更可靠的捍衛基督教並闡釋其基本內容的方式,並非從那些表達基督教一些最廣為人知的歷史變體的基本信條認信的術語出發,而是從那些最充分表達並賦予基督教作為救贖宗教之特徵的術語出發。換句話說,除非將基督教視為源自聖父、聖子和聖靈的聖約旨意和目的,並在其實現中得到完滿成全,否則就無法正確理解基督教,也無法對其闡述作出適當的定位。」4 我們不應該根據基督教的最低形式,而應根據其最高形式來定義基督教的本質。加爾文主義是「基督教的自我實現」(Calvinism is “Christianity come to its own.”)。 我們應該從加爾文主義出發,一路下行到普世主義更正教,再到羅馬主義,因為它們都偏離了基督教真正的觀點。
我們現在主要關注的是羅馬主義。羅馬主義應被視為基督教的變形(deformation),事實上是其最低層的變形。而這種變形不僅表現在某些教義點上,而是表現在每一個教義點上。如果我們說路德恢復了教會關於聖經、因信稱義和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正教義,那麼更正教與羅馬主義之間的差異就沒有得到充分說明。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在於,更正教在每一個教義點上都更一致地持守基督教信仰,而羅馬則不那麼一致。情況不可能反過來。教義上的某一點若有不一致,必然會導致所有教義上的不一致。羅馬在教義表達的全部範圍內,一直都在混淆非基督教與基督教的教導元素。
現在可以簡要談一談這一切對「出發點」問題的影響。在出發點問題上,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擁有真正基督教的人論(doctrine of man)。但羅馬教會並沒有這樣的教義。無需贅述,我們可以斷言羅馬教會的教義是有缺陷的,(a) 關於人受造時的本性,以及(b) 關於罪進入人性後所產生的影響。查爾斯·賀治(Charles Hodge)說:「重要的分歧點是,更正教徒認為原初的義(original righteousness),就其包含亞當的道德卓越而言,是「自然」的,而羅馬主義者則主張它是「超自然」的。根據他們的理論,上帝創造了人的靈魂和身體。這兩種構成人性的組成要素是相互衝突的。為了保存它們之間的和諧,以及肉體對靈性的恰當順服,上帝就賜給了人『原初的義』這一超自然恩賜(譯按:即額外的恩賜,supperdonum additum)。人在墮落中失去的正是這個恩賜;因此,自背道以來,人就處於亞當被賦予這種超自然恩賜之前的狀態。與此教義相反,更正教徒則主張『原初的義』是與人同時受造的(concreated),而且是自然的。」5 賀治列舉了反對羅馬觀點的理由:(1) 「它預設了一種貶低我們本性中的原始構造(original constitution)的觀點。根據這種教義,邪惡的種子從上帝手中就被植入了人類本性之中。人類本性是無序的或有病的,存在著貝拉明(Bellarmin)所說的「病態」(morbus)或「慵懶」(languor),需要某種補救……」(2) 「這種關於原初的義的教義源於羅馬教會的半伯拉糾主義,且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種半伯拉糾主義。」6
那麼,假設一個羅馬主義者接近一個非信徒,並邀請他接受基督教。在他看來,非信徒僅僅是失去了原初的義的人。正如賀治所說,根據羅馬主義的說法,在非信徒身上的上帝形象,「僅僅在於人的理性,尤其是人的意志本性(voluntary nature),或者說是意志的自由」,而且被認為仍然完好無損。也就是說,這位非信徒對自己智力和意志能力的看法,除了極端情況外,或許是正確的。非信徒或屬血氣之人(直譯:自然人)在運用其知識和行動能力方面所做的一切,並不必然涉及任何罪(譯按:即「中立的」)。按照這種觀點,屬血氣的人不需要基督教的光照就能正確地理解世界、理解他自己。他不需要聖經的啟示或聖靈的光照,以便透過它們了解自己的真實本性。
因此,在此基礎上,基督教就必須向屬血氣之人呈現為僅僅是附加在他已經擁有的知識之外的信息。基督教的知識應與人運用理性和觀察能力所獲得的知識連結起來,其方式類似於起初上帝將原初的義加在人身上的上帝形象上。
然而,若沒有基督教的光照,人就幾乎不可能對自己和世界有正確的認識,正如他不可能對上帝有正確的認識那樣。由於罪是真實存在的,無論真理出現在哪裏,人都會對真理視而不見。而真理是一體的(truth is one)。人若不真正認識上帝,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加爾文說,哲學家不承認墮落的事實,便將一切都搞亂了。他們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起初靈魂的每一部分都被塑造為正直」,但墮落之後,人在其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同樣敗壞了。7 加爾文說:「他們告訴我們,靈魂的有機運動與理性部分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彷彿理性本身就不會自相矛盾,它的各種籌謀有時甚至像敵對的軍隊一樣相互衝突。然而,既然這種混亂肇因於本性的墮落,因此,僅僅因為這些功能沒有像它們應該的那樣和諧一致,就推斷出有兩個靈魂,是錯誤的。」8
因此,關於人性中的「紊亂」(disturbance),其起源和本質問題的看法,羅馬主義和加爾文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羅馬的觀點與希臘哲學家,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基本一致。根據這種觀點,紊亂是人性固有的,因為人的一部分是由非理性元素所構成的。人只要擁有理智,就不會、也不能犯罪。人性中的「紊亂」主要不是源於自己的過錯,而是根本源於「造」他的「上帝」。另一方面,加爾文認為,人從上帝手中造出來時,其本性中並無「紊亂」。「紊亂」是作為罪的結果而進入的。因此,墮落之人的每一種功能都失靈了。整個人格傾向都改變了。墮落之人的理智本身可能足夠敏銳。因此,它能夠從形式上理解基督教的立場。它好比一把鋒利閃亮的電鋸,隨時準備好切割運送到它面前的木板。比方說,一個木匠想要切割五十塊木板來鋪設房屋的地板。他已經在木板上做了標記,也調整好了他的電鋸。他從木板上標記的一端開始切割。但他不知道他七歲的兒子動了電鋸,改變了它的設定。結果是他鋸的每一塊木板都是斜切的,因此除了鋸子最初接觸木材的那一點之外,其他部分都因太短而無法使用。只要電鋸的設定沒有改變,結果就始終如此。同樣,每當基督教的教導呈現給屬血氣之人時,它們都會按照有罪的人格傾向被切割。人的智力越敏銳,基督教的真理就越會一致地按照一種純粹的內在論模式(immanentistic pattern)被切割。結果是,無論他們在形式上多麼理解基督教的真理,他們仍然崇拜「自己內心的夢想和虛構」。9他們擁有賀治所說的「單純的認知」(mere cognition),卻沒有對上帝的真知識。
此外,正如「哲學家」和加爾文對人性中「紊亂」的來源和本質的看法存在分歧,他們在消除這種紊亂所採用的補救措施上也有不同意見。按照哲學家的看法,人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幫助來消除內在的紊亂。而按照羅馬在很大程度上所遵循的希臘觀點,人的理智本身就具有正確的設定。墮落並沒有擾亂電鋸的設定,因此並不需要聖靈的超自然能力來重新調整它。理智的本質及其活動幾乎不受人類在歷史進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事情的影響。
與這種觀點相反,賀治遵循加爾文的引導強調這個事實,即有罪之人的整個傾向需要被聖靈的能力更新。屬血氣之人必須「在知識上得以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10)。賀治在解釋聖保羅時說到:「新人(νέος),按照νέος和καινός之間通常的區別,意味著最近的、新造的,與(παλαίος)舊的相對。這個新近形成的人的道德品質或卓越性,是用ἀνακαινούμενον這個詞表達的;正如在聖經用法中,καινός是純潔的。這種更新被稱為εἰς ἐπίγνωσιν,不是在知識中,更不是藉著知識,而是達到知識,使他知道。知識是所說的更新所獲得的果效。」10 賀治稍後補充說:「這裏所指的知識不是僅僅的認知。它是完全的、準確的、活潑的或實踐的知識;這種知識就是永生,因此這個詞在這裏包括以弗所書四章24節中用仁義和聖潔所表達的內容。」11
賀治也解釋了以弗所書四章24節「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righteousness)和聖潔(holiness)。」賀治說:「這些詞組合在一起使用時,意在窮盡一切;即涵蓋所有道德上的卓越品質。任何一個詞都可以在這種全面的意義上使用,但是,當區分時,δικαιοσύνη意味著正直,是正確的和做正確的事,正義(justice)所要求的;ὁσιότης,純潔,聖潔,當靈魂充滿上帝時產生的心靈狀態。使徒的話不應該翻譯為『真正的聖潔』(true holiness),而應該翻譯為『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也就是說,仁義和聖潔是真理的果效或表現。這裏的真理,與第22節中提到的詭詐(ἀπάτη)相對(《和》迷惑),意思就是在歌羅西書三章10節中所稱的知識。它是悟性中的神聖之光,真理的靈是其作者,所有正確的情感和聖潔的行為都從中作為其近因(proximate cause)而產生。」12 賀治再三強調,根據聖經,屬血氣之人本身無法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屬血氣之人,就本性而言的人,缺乏上帝的生命,即屬靈的生命。他的悟性是黑暗的,因此他不認識或接受上帝的事。他對屬靈世界的實在不敏感。他對它們就像死人對這個世界的事物一樣無知無覺。」13 在討論重生時,賀治斷言:「聖經認為永生在於知識,罪性是盲目或黑暗;從罪惡狀態到聖潔狀態的轉變,就是從黑暗走向光明;人被稱為在知識上得到更新,意即知識是重生的果效,悔改被視為是藉著基督的啟示而成就的;拒絕承認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和人類的救主,被歸因於不信者的眼睛被這世界的神蒙蔽了雙眼。」14 或者再次說:「聖經中的心是思考、感受、行使意志和採取行動的。它是靈魂,是自我。因此,新心就是新的自我,新人。它意味著整個品格的改變。它是新的本性。一切有意識的、自願的、道德的活動都從心裏發出。因此,心的改變是一種在這些活動之前並決定其品格的改變。」15 「根據福音派的教義,整個靈魂是重生的主體。它既不是排除感情的理智,也不是排除理智的感情;也不僅僅是意志,無論是在其更廣泛還是更有限的意義上,是所討論的改變的主體……」16 「重生確保了正確的知識以及正確的感受;正確的感受不是正確知識的果效,正確的知識也不是正確感受的果效。兩者是影響整個靈魂工作的不可分割的果效。」17
賀治再三強調,根據聖經,屬血氣之人本身無法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真理。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羅馬天主教護教學試圖透過知識上的「共同領域」(common area),與非信徒建立接觸點,這是自然且前後一致的。羅馬天主教神學同意那些它試圖贏得歸向基督教信仰的人的基本主張,即人對自己和世界一切物體的意識,無需提到上帝也可以理解。
但這正是羅馬主義和更正教之間根本差異所在。根據更正教的原則,人的意識若想要瞭解自我、瞭解客體,必須以上帝的自我意識為前提。在斷言這一點時,我們考慮的並不是心理和時間上的優先性,而只是在思考詮釋的最終參照點是什麼。更正教的原則認為,此最終參照點在於自足的本體三一(ontological trinity)。藉著祂的旨意,三一上帝掌管著即將發生的一切。因此,就事情的本質來說,即使人的意識必然是最直接的起點,然而,上帝始終是最根本的,因而也是人類詮釋的最終或終極的參照點,這一點是始終不變的。
歸根究柢,這關乎一個人的終極預設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當人成為罪人時,他就使自己而不是上帝成為終極或最終的參照點。而必須受到質疑的恰恰是這個預設,因為它無一例外地支配著所有形式的非基督教哲學。如果這個預設在任何領域都未受到質疑,那麼呈現在非信徒面前的所有事實和論證都將被他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加以扭曲。罪人給自己的眼睛牢牢地粘上了有色眼鏡,是他無法摘除的。而在罹患黃疸病的病眼中,一切都是黃色的。除非參與推理的人彼此理解對方的用語是什麼意思,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可理解的推理。
屬血氣的人若不質疑這個基本預設,以他自己作為作出斷言(in predication)的最終參照點,他可能會接受「有神論的證明」是完全有效的。他可以構建這樣的證明。他也已經構建了這樣的證明。但是以這種方式向自己證明其存在的神明,永遠是一個不同於聖經中自足的本體三一的上帝。羅馬天主教護教者不想證明這種上帝的存在。他想要證明的是這樣的一位上帝的存在,這位上帝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完整地保留人的自主性。羅馬的神學並不希望有這樣的上帝,祂的旨意能掌控一切將要發生的事。
因此,羅馬對與非信徒接觸點的看法是如今這個樣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貳、福音派
我們已經談到了羅馬主義和更正教在接觸點問題上的基本差異。但並非所有更正教都完全忠於更正教原則。華腓德在所討論的書中出色地指出了這一點。只有在加爾文主義中,救恩唯獨出於上帝這一更正教原則才得到一致的表達。非加爾文主義的更正教徒,經常被稱為福音派,以「普世主義的視角」構想了「上帝為救恩所做的工作」(the operations of God looking to salvation universalistically),以便為個人最終的抉擇留出空間。18上帝彷彿透過基督在銀行裏存入了一大筆錢,並在報紙上刊登公告,向每個前來的人提供足以滿足他一切需要的錢。那麼,歸根究柢,個人是否願意成為並繼續留在靠這家銀行的慷慨而生活的人的行列中,則取決於個人。上帝透過普遍性(universals)接近人。福音派信徒之間存在差異,但歸根究柢,這些分歧僅僅在於上帝是透過更廣泛的還是更狹義的方式來接近個體。最終的決定權始終留給了個人。「因此,救恩過程中的特殊主義就成為加爾文主義的標誌。」19 因此,華腓德將加爾文主義稱為更正教「未受外來侵入元素污染」的唯一形式。上帝的行動是一切確定存在的終極根源。
非加爾文主義的更正教徒,經常被稱為福音派,以「普世主義的視角」構想了「上帝為救恩所做的工作」(the operations of God looking to salvation universalistically),以便為個人最終的抉擇留出空間。
因此,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點是,福音派在人論和神論上都保留了羅馬天主教的某些觀點。像羅馬主義一樣,福音派認為,人的自我意識和對客體的意識在某種程度上無需借助上帝的意識也能被理解。可以預見,福音派在接觸點的問題上,會與羅馬天主教達成一致。這兩種神學形式都帶有某種潛在的自然主義元素的色彩。因此,兩者都不願意挑戰屬血氣之人關於他自己作為最終詮釋參照點的基本預設。兩者都不願意證明存在著一位掌管著將要發生的一切的上帝。
福音派護教學的偉大教科書是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著名的《類比》(Analogy)。在這裏,我們的目的不是充分處理其論證。只需指出其論證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反異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中的論證非常相似就足夠了。巴特勒在神學上持亞米念主義觀點。因此他認為,屬血氣之人憑著「合理地運用理性」,就可以正確地解釋「自然的運行規律和構造」。只要屬血氣之人繼續運用相同的「合理地運用理性」,來理解聖經中向他呈現的關於基督及其工作的事實,他就極有可能成為基督徒。20
叁、半吊子的加爾文主義(Less Consistent Calvinism)
因此,出發點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的神學立場。在本書的前幾章中,我們的目標是根據改革宗信仰的原則,闡述基督教的顯著特徵。具體來說,我們的目標是按照近代偉大的改革宗神學家的指示,說明基督教的主要特徵。我們正是基於查爾斯·賀治、赫爾曼·巴文克和華腓德等人(這裏僅列舉部分)的著作,勾勒出改革宗生活與世界觀的大致輪廓。只有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我們才能建構出一個相對連貫的更正教主義(Protestantism)。
如果我們在護教學和神學本論(theology proper)中都遵循他們的原則,那麼,我們只需採納他們的建議即可。正如華腓德本人如此精確地表達的那樣,我們要捍衛的並非基督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本質,也不是基督教教義所包含的每一個細節,而「正是基督教本身……包括其所有『細節』,並涵蓋其『本質』——以其未經闡明和未壓縮的整體……」21
我們必須將這基督教帶給那些死在過犯罪惡中的人。華腓德說:「公義的在死者的場域上,太陽已然升起,宣告祂降臨的歡呼聲卻落在聾子的耳朵上;是的,即使晨星應該再次因喜樂而歡唱,空氣中迴蕩著偉大宣告的迴響,它們的聲音也無法穿透死人的耳朵。當我們環顧著充滿邪惡的世界時,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正是先知異象中的山谷:一個充滿骸骨的山谷,看哪!它們如此乾枯。即使是最偉大的救贖,向枯骨宣告又有什麼益處呢?我們怎能站立,呼喊著,哦,你們這些枯骨啊,聽耶和華的話!除非有氣息從天而降,吹拂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過來,否則無論是救贖,還是宣告,都將徒勞無功。」22「基督徒憑藉賜給他的生命而活,當然,在那生命開始之前,他沒有任何行動的能力;身為基督徒,對於我們救恩的超自然性所作的見證,我們不應該輕描淡寫,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23 我們已經看到賀治論證說,重生就是得到知識、仁義和聖潔。
當賀治談論宗教事務中的理性時,我們似乎已從這個高階層面跌落到福音派的水平。在這個標題下,他提出了三點。首先,他表明理性是接受啟示的必要工具。關於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的餘地。「啟示不可能是給野獸或給白癡的。」24 其次,賀治主張,「理性必須判斷啟示的可信度。」25 而「可信的就是可以被相信的。除了不可能的事,沒有什麼是不可信的。凡可能的事,就可以理性地(即基於充分理由)被相信。」那麼,什麼是不可能的呢?賀治回答說:「(1) 凡涉及矛盾的事就是不可能的;例如,某件事既存在又不存在;對的是錯的,而錯的是對的。(2) 上帝會做、認可或命令任何在道德上錯誤的事,是不可能的。(3) 祂不可能要求我們相信任何與祂刻印在我們本性中的信仰法則相矛盾的事。(4) 一個真理不可能與另一個真理相矛盾。因此,上帝不可能啟示任何已被充分證實的真理相矛盾的事,無論這些真理是直覺、經驗或先前的啟示。」第三,賀治繼續說到,「理性必須對啟示的證據作出判斷。」因為「信心包含同意(assent),而同意是由證據產生的確信,因此沒有證據的信仰要麼是非理性的,要麼是不可能的。」賀治說,理性的第二和第三特權都得到了聖經本身的認可。保羅「承認心智所作的直覺判斷的最高權威」,而「耶穌則以祂自己的作為來證明祂所宣稱的真理。」
我們在此的目的不是要全面探討理性與啟示的問題。只需指出處理這種接觸點問題的方式背後的含糊性就足夠了。賀治所說的理性,指的是「上帝植入我們本性中的那些信仰法則」。當然,上帝確實將這些信仰法則植入了我們的存有之中。當加爾文說所有人都有神性意識(a sense of deity)時,他所強調的就是這一點。然而,不信者並不接受他自己是按上帝形象受造的教義。因此,要訴諸於人的智性和道德本性——正如人自己對這種本性的詮釋——並要求它必須判斷啟示的可信性和證據,就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做,我們實際上是在告訴屬血氣之人,只要他願意接受基督教,就讓他按照他對人性的扭曲概念所能接受的程度去接受,再多一分也不必。
再以鋸子為例:鋸子本身只是一種工具。它能否運轉,能否朝著正確方向切割,取決於操作它的人。同樣,理性或智力以始終是人的工具。而運用理性的人,不是信徒,就是不信者。如果他是信徒,正如賀治告訴我們的,他的理性已經因重生而改變了其設定。那此時,它就不能成為審判者;它現在是重生之人的一部分,樂意服從於上帝的權柄。它已經因著上帝的恩典,讓自己被上帝的啟示所詮釋。另一方面,如果運用理性的人是不信者,那麼這個人運用他的理性,肯定會以審判者的立場來判斷啟示的可信度和證據,但他也肯定會發現基督教難以置信,因為它根本不可能,並且支持它的證據總是不足。賀治自己關於屬血氣之人的盲目和剛硬的教導也證實了這一事實。將判斷什麼是可能或不可能的權利賦予屬血氣之人——透過他的理性,或透過他的道德本性判斷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實際上就是否定「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而賀治與華腓德一樣,都相信特殊主義正是真正合乎聖經的神學的標誌。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就不會聲稱自己能夠詮釋理性者本身。那個理性者會被視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就被認為已經在自己裏面擁有正確詮釋和正確運用自身本性之權能的能力。而這與亞米念主義的立場完全一致,即聲稱上帝只是使救恩在客觀上成為可能,然而實際上並沒有拯救個別的人。
如此,賀治在接觸點問題上的立場的主要困難在於,它沒有清晰地區分人類的原初本性和墮落本性。當然,賀治的根本意圖是訴諸於人從造物主手中誕生時的原始本性。但他經常論證說,這種原始本性彷彿仍然可以在人的「普遍意識」(common consciousness)中找到,而且十分活躍。誠然,人類的常識並沒有像哲學家的詭辯那樣偏離真理,這種說法本身不無道理。公開的、褻瀆上帝的無神論通常不會出現在大眾之中。但這並不能排除一個事實,即所有人在其位格的所有表現中,都帶著罪性。
我們來作一個比較,或許有助於澄清這一點。在羅馬書第七章中,保羅談到自己雖然是信徒,但在他的肢體中卻有罪的律,經常違背他的意願控制著他。他的「新人」是真正的人,是在基督耶穌裏的人。但他的「舊人」則是他的罪性中尚未完全被肅清的殘餘。將這個類比應用於屬血氣之人身上,我們就會明白,這個罪人是他裏面的「新人」是與撒但結盟的人。而他的「舊人」則是在他肢體中與他的意志相爭的;那是他從造物主手中誕生時的本性。當浪子離開父家時,他就如同走向了豬槽。但在路上,他心裏忐忑不安。他試圖說服自己,他的真正本性在於堅持自我,遠離父家。但他卻自討苦吃(原文直譯:用腳踢刺,參徒廿六14)。他明知故犯地犯了罪。
賀治神學的精髓在於,它訴諸罪人身上的「舊人」,而訴諸於罪人身上的「新人」——彷彿後者就能對任何問題作出基本正確的判斷——則完全違背了他的神學理念。然而賀治未能清楚地區分這兩者。因此,他未能清楚地區分改革宗、福音派、羅馬天主教關於接觸點的各種觀點。因此,他也談論「理性」,彷彿它是無論出現在哪裏都能正確運作的東西。但有罪之人的「理性」,總是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尤其是當他們面對聖經的具體內容時,更是如此。屬血氣之人將始終使用他的理性工具,將這些內容簡化到自然主義的層次。即使是為了顧及矛盾律,他也必須這樣做。因為他自己的終極性是他整個哲學最基本的預設。他正是以這個預設作為支點,來使用矛盾律的。如果要求他運用理性來判斷基督教啟示的可信度,同時又不要求他放棄自我至上的觀點,那麼實際上就是要求他在同一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既相信又不相信他自己的終極性。此外,這個人除了以矛盾律為由拒絕基督教外,還會以他所謂的「自由直覺」(intuition of freedom)的名義拒絕基督教。他所謂的自由直覺,實際上與他的終極性是同一回事。談到那些「哲學家」時,加爾文說:「他們提出的原則是,人若沒有自由選擇善惡的能力,否就不能成為理性的動物。……他們還認為,如果人不是憑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那麼美德與邪惡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26如果要求這樣的人要求接受基督教的立場——根據這個立場,他的命運最終由上帝的旨意決定——就是要求他接受對他而言使對的變成錯的、錯的變成對的的立場。
若我們不憑任何抽象概念——無論是理性還是直覺——來尋找接觸點,就不過是遵循賀治在其神學中、追隨加爾文所給出的指引。在人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抽象概念。我們面對的始終是具體的個體。這些人都是罪人。他們「心懷不滿」(have “an axe to grind.”),企圖用不義壓制真理。他們會運用他們的理性來達到此目的。若我們承認人的終極性,那麼他們拒絕基督教的教導,在形式上就並非不合邏輯。恰恰相反,為了保持邏輯的自洽,他們非如此不可。這一點將在後文中更充分地探討。目前,我們只需指出,護教者如果訴諸某種形式的「人類普遍意識」,他就不僅違背了自己關於人作為上帝受造物的教義,更會適得其反,徹底挫敗其護教的目的。
護教者如果訴諸某種形式的「人類普遍意識」,他就不僅違背了自己關於人作為上帝受造物的教義,更會適得其反,徹底挫敗其護教的目的。
在繼續討論我們認為更符合聖經關於接觸點問題的觀點之前,我們想提請讀者注意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另一種立場不一致的加爾文主義形式。在他的著作《聖靈的見證》(Het 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中,瓦倫丁·赫普(Valentine Hepp)博士談到關於上帝、人和世界的「第一原理」(prima principia),他說,人們普遍接受這些原理。對於從創造本身就向我們說話的一切核心真理,人們幾乎毫不懷疑。少數錯誤的科學家堅持維持他們錯誤的出發點,並堅稱他們懷疑上帝、人或世界是否存在。他們之所以這麼說,並非出於經驗,而是出於他們自己的系統。儘管我們經常聽到他們的說法,但他們的數量其實非常少。總的來說,人類並不否認這些核心真理。絕大多數人承認存在著一種凌駕在他們之上的更高的力量,並且毫不猶豫地接受世界和人的真實存在。27 即使從這段引文中來看,赫普的立場也與賀治的立場相似。與賀治一樣,赫普也想訴諸於一種普遍存在的對「核心真理」的信仰,這種信仰是所有人在不太世故的情況下都會接受的。對赫普來說,正如對賀治一樣,似乎存在這某種常識性的哲學,這是屬血氣之人所擁有的哲學,而且因為是直覺的或自發的,所以迄今為止,尚未受到罪的玷污。然而,即使從這段簡短的引文也能看出,人類的「普遍觀念」(common notions)本身就是有罪的觀念。人反思自己對意義的感知,然後僅僅說存在一種更高的力量、一個上帝,實際上就是在說上帝不存在。這就好比一個孩子,反思他的家庭環境後會得出結論說,存在著一個父親或一個母親。而「承認世界和人的真實性」本身甚至不能算是承認創造和護理的基本真理。僅僅從非基督徒思想家更高度闡述的系統訴諸於普遍意識的哲學、常識的哲學、直覺的哲學——即訴諸於與人類所承受的啟示壓力更為直接相關的某些事物——是遠遠不夠的。赫普和賀治似乎都只想效法加爾文,訴諸於人人心裏都有的神性意識。然而這種旨在闡述保羅的教導——即上帝的啟示臨在每個人心裏——的觀念,必須與有罪之人對這種啟示所作出的反應仔細區分開來。上帝的啟示,而非某個神明的啟示,是如此直接地臨在於每個人身上,以至於,正如華腓德追隨加爾文所說的:「對上帝存在的確信帶有直覺真理的標記,因為它是人類普遍且不可避免的信仰,並且與自我觀念在同一行動中同時被賦予。自我立即被視為依賴的,也是負責的,因此它暗示著一位它所依賴並對其負責的對象。」28正是這種神性意識,甚至是對上帝的認識——保羅告訴我們(羅一19-20),每個人都擁有這種認識,但正如保羅也告訴我們的,每個罪人都試圖壓制這種認識——才是基督教護教學必須訴諸的對象。
到目前為止所說的內容可能看起來極其令人沮喪。似乎迄今為止的論證已經迫使我們徹底否認與不信者有任何接觸點。人們若想進一步了解真理,不是必須與真理有某種接觸嗎?如果人們對真理一無所知,又怎麼可能對它產生興趣呢?如果人們完全瞎眼,為什麼要在他們面前展示光譜的顏色呢?如果他們耳聾,為何要帶他們去音樂學院?
此外,理性本身不是上帝的恩賜嗎?科學家雖然不是基督徒,難道不也對宇宙了解很多嗎?難道一個人必須成為基督徒才能知道二乘二等於四嗎?而且除此之外,基督教雖然告訴我們許多超越理性的事物,難道也要求我們接受任何違背理性的事物嗎?
我們對這類質疑的回答是,正是在改革宗關於接觸點的概念中,而且唯獨在其中,才能避免歷史上著名的關於全然無知或全然全知的兩難困境。但在明確論證這一點之前,有必要指出在羅馬天主教的觀點中,這一困境是無法解決的。
如果一個人對真理一無所知,他就不可能對真理感興趣。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對真理感興趣,那麼他必定已經掌握了真理的主要元素。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兩難困境,羅馬天主教和福音派更正教菜試圖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的某種「普遍知識」領域中尋找接觸點。他們的論點是,加爾文主義者以他們的方式教導人的全然敗壞,卻不幸地陷入必須對著聾子傳福音的境地。然而,我們相信,只有加爾文主義者才不會陷入這種境地。
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可以說明羅馬天主教的立場。這個洞穴裏的居民脖子和腿上都戴著鎖鏈。他們只能看到影子,並將回聲歸因於這些影子。然而他們卻認為,「他們所起名的,正是眼前真實存在的事物」。柏拉圖說,如果他們當中有人被釋放,他會需要適應太陽光。但他會同情那些仍然被困在洞穴裏的人。而且「如果他不得不與從未離開洞穴的囚犯比賽測量影子……在他們眼裏,他豈不是滑稽可笑嗎?」「人們會說他上去又下來,卻沒了眼睛;甚至連想都別想要上去;如果有人試圖解開另一個人的鎖鏈,把他帶到陽光下,只要當場抓住這個犯法者,他們就會把他處死。」
柏拉圖本人將這則寓言與人認識真理的能力和對真理的認識聯繫起來解釋。囚犯有眼睛可以看到真理;他們所需要的只是把頭轉過來,這樣他們就可以面對真理。
羅馬天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看待屬血氣之人的。托馬斯·阿奎那沿襲亞里士多德的一般推理方法,主張屬血氣之人可以憑藉其理性的正常使用,就能恰當地對待他周圍的自然啟示。他只需要一些幫助,以就能正確地理解並對基督教中所蘊含的超自然啟示作出正當當反應。
那麼,根據羅馬天主教的觀點,屬血氣之人已經擁有真理,即對自然啟示的正確詮釋。他之所以正確地詮釋自然啟示,是因為他參與了上帝的存有。當然,這裏所說的擁有真理,僅是指對自然啟示的詮釋而言。但是,如果屬血氣之人能夠並且確實以一種本質上正確的方式詮釋自然啟示,那麼他就沒有理由說他需要超自然的幫助來正確詮釋基督教。他最多只需要知道基督和祂的聖靈已經來到世上。聽到這個消息,作為一個理性的存有者,他必然會對此作出適當的反應。如果屬血氣之人的眼睛(理性)使他能夠在某個維度上正確地看待事物,那麼就沒有充分理由認為,同樣的眼睛不能使他在沒有然後外力的進一步幫助下,就能在所有維度上正確地看待事物。洞穴裏的所有囚犯完全有理由可以掙脫枷鎖,行走在陽光下。事實上,柏拉圖並未說明為何那些未能逃脫的人不能像那個逃脫的人一樣成功逃脫。
另一方面,可以說根據羅馬天主教的觀點,屬血氣之人並沒有給出對自然啟示完全正確的詮釋。托馬斯·阿奎那不是糾正了「哲學家」對自然事物的詮釋嗎?羅馬天主教關於人身上有上帝形象的觀點本身難道不是在暗示,即使在墮落之前,如果人沒有附加恩賜(donum superadditum),就無法完美地認識任何事物嗎?
我們回答說,儘管阿奎那確實糾正了亞里士多德的一些結論,但他仍然接受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認為它本質上是健全的。但是,暫且忽略這一點,為了論證起見,根據羅馬天主教,我們姑且認為屬血氣之人對自然啟示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那麼,應該指出的是,羅馬天主教對此唯一能提出的理由是啟示本身存在缺陷。我們不能因為柏拉圖洞穴的囚犯只能看到影子就責怪他們。就他們所處的位置來說,他們已經盡到了應有的責任。如果他們的頭部受到約束,以至於只能看到影子,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這是自然構造和自然進程使然。根據這個觀點,人的心智原本就無法自然地接觸真理。羅馬神學所持有的自由觀念,是基於人與「神明」在形而上學上本來就是不同的。這等同於說,人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他沒有「存有」。在此基礎上,自然啟示與屬血氣之人的心智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真正的接觸點。人與上帝失去了接觸,和人參與在上帝的存有中,這兩種觀念是相互依存的。
我們並不反對「人的心智總是需要超自然啟示」這種觀念。相反,我們要強調的事實是,即使在樂園中,人的心智也需要並享受超自然啟示。我們反對的是,對於人即使在樂園中也需要超自然啟示這個現象所作的解釋。根據羅馬天主教的觀點,這種需求的理由,實際上是人的原始構造中的缺陷(與生俱來的缺陷)。這意味著,人按照其原初的構成,本性上既傾向於犯錯,也容易獲得真理。其原因是,羅馬天主教的上帝並沒有掌管「一切將要發生的事」。因此,人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啟示出上帝的事物。人也面對終極的非理性事物。在這種對現實的普遍理解下,很自然地會認為人的本性(原文:人的構成)一方面擁有真理,另一方面卻又永遠無法透過其自然行動獲得真理。
在這個基礎上,即使把超自然啟示加在自然啟示之上,也無法解決問題。無論對超自然啟示還是對自然啟示來說,都同樣如此:要麼根本無法被人類理解,要麼即使被人理解了,人也不需要它。
如果自然啟示沒有如此包覆著人,以至於使他不可能察看任何不述說上帝的事物,那麼超自然啟示也同樣做不到這點。如果自然啟示沒有述說這樣一位上帝——祂的旨意完全環繞人,那麼超自然啟示也無法述說這樣一位上帝。但如果它竟能(這實屬不可能)述說這樣的一位上帝,那麼,對羅馬天主教所設想的人類心智來說,也毫無意義。一位自足的上帝所發出的啟示,對一個認為自己終極上是自主的心智來說,可以是毫無意義的。存在接觸點的可能性已然消失。如果人自己是自主的或自足的,那麼,聖經中自足的上帝的啟示的整個觀念就崩塌了。如果人的內在存有結構本身不具啟示性,便無法接受來自外部的任何啟示。
另一方面,如果人在任何意義上是自主的,他就不需要啟示。如果說他擁有真理,那也是他憑藉自己智力的最終立法能力所獲得的真理。只有當他能夠透過運用不矛盾律來實際上控制周遭的一切現實的事實時,他才能認識任何真理。因此,如果他以這種方式認識了任何真理,他實際上就認識了所有的真理。
那麼,在羅馬天主教的立場上,人就如同柏拉圖的洞穴居民,憑藉其自身的構造,已經適應了半黑暗的環境。啟示對他沒有任何益處,即使我們或許認為他需要它。如果啟示要臨到他,那也必須像真理臨到柏拉圖洞穴裏的某個居民那樣,以一種偶然的方式降臨。否則,人就如同柏拉圖筆下那個偶然獲得解放的洞穴居民一樣,並不需要超自然啟示;在他觸手可及之處,潛在地擁有了一切真理。
肆、改革宗立場
現在應該清楚了,只有完全合乎聖經的接觸點的概念,才能擺脫絕對無知或絕對全知的困境。
如前所述,羅馬天主教和亞米念主義觀點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它將終極性或自足性歸於人的心智。羅馬主義和亞米念主義在其系統神學著作中所闡述的人觀都是這樣做的。因此,對他們而言,不去挑戰不信者所作的終極性假設是立場一致的。然而,改革宗神學,如加爾文及其近代闡釋者,如賀治、華腓德、凱波爾和巴文克,都認為人的心智是衍生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與上帝的啟示有接觸。它只被啟示所環繞。它本身就具有啟示性。按照本性,若不能意識到自己的受造性,它即無法意識到自己。對人來說,自我意識預設了對上帝的意識。加爾文稱之為人無法擺脫的神性意識(sense of deity)。
對身處樂園的亞當來說,對上帝的意識不可能在三段論推理過程的結尾才出現。對他來說,對上帝的意識是他對一切事物的推理具有意義的前提。
創造論必須用盟約概念來補充。人受造為歷史性的存有。從歷史之初,上帝就將一項責任和任務放在人身上,就是要把上帝在創造中所表達的旨意,以個體和集體的方式,對著人自己重新作出詮釋。因此,人的受造意識可以更具體地標示為盟約意識。但在樂園中,盟約的啟示是以超自然的方式,藉著中介傳達給人的。這自然是這種情況,因為它與人的歷史任務息息相關。因此,順服或悖逆的意識直接涉及到亞當對自己的意識。盟約意識包覆著受造意識。在樂園中,亞當知道,身為上帝的受造物,他自然而然地、理所當然地應該遵守上帝與他立的盟約。由此可見,即使在樂園中,人自身的自我意識也依賴於他與超自然啟示、自然啟示的接觸。上帝的自然啟示既在人裏面,也在人周圍。人作為理性和道德的存有,其自身的構造就是對人的啟示,而人負有倫理責任,要對啟示作出回應。然而,自然啟示本身並不完整。它從一開始就需要以關於人本性的超自然啟示加以補充。因此,超自然啟示的觀念本身,相互依存地體現在人自身的自我意識的觀念中。
正是以這種方式,可以說人憑藉其原初的構成與真理有接觸,但尚未擁有全部的真理。人不在柏拉圖的洞穴裏。他並非處於一種反常的境地,明明有雙眼可以看見,卻仍住在黑暗中。他不像柏拉圖筆下的洞穴居民那樣,僅僅擁有某種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的認識真理的能力。人最初不僅僅擁有接受真理的能力;而且實際上擁有真理。真理的世界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就在他面前。向他的感官說話的,與向他的智力說話的,同樣都是上帝的聲音。即使他閉上雙眼,不去注意外部世界,他內在的感知也會在他自己的構造中向他把上帝顯明出來。他經驗的實質(matter)並不需要任何形式(mere form)來組織這些原始素材。相反,他經驗的實質從內到外都被照亮了。然而,照亮它的正是上帝自願的作為,上帝的旨意使事物成為如今的樣貌。人若意識到自己,就必然會意識到周遭的事物,也會意識自己肩負的責任,就是為上帝的榮耀管理自己、管理萬物。人對事物和自我的意識並非靜止不動的,而是存在於時間之中的意識。此外,這種存在於時間之中對事物和自我的意識,意味著對歷史的意識,以及對歷史背後上帝計劃的意識。人最初的自我意識暗示出對上帝臨在的意識,人要為上帝完成一項偉大的使命。
只有當我們透過這樣分析人墮落之前樂園中的狀況入手,來探討接觸點的問題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屬血氣之人,以及其認識真理的能力。使徒保羅談到屬血氣之人實際上擁有對上帝的知識。他的罪的嚴重性恰恰在於「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祂。」(譯按:羅一21)沒有人能躲得掉認識上帝。認識上帝與他對任何事物的感知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正如加爾文所說,人應該承認上帝。若不如此,他就毫無任何藉口可言。他不承認上帝的原因,完全在於他自己。這是因為他蓄意違背了自身存有的法則。
羅馬主義和更正教福音派都未能完全公正地處理保羅的這一教導。實際上,它們兩者都未能讓人完全被上帝的啟示所環繞。由於他們不堅持上帝的旨意是掌管萬有的,因此無法教導人的自我意識總是以對上帝的意識為前提。根據羅馬天主教和福音派的觀點,人對周遭的事物以及對自己與這些事物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知覺,卻未必同時覺察到自己有責任在與上帝的關係中駕馭這兩種意識。因此,人對事物、自我、時間和歷史的意識,並非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上帝的完全依賴關係上。因此,就有了這些眼淚(Hinc illae lacrimae)!(譯按:指人類因此落入悲慘的境地。)
當然,當我們這樣強調保羅的教導——即所有人不僅僅有能力,而且實際上擁有對上帝的知識——時,我們必須立即補充保羅的進一步教導,即所有人由於內在的罪,總是在各種關係中試圖「壓制」這種對上帝的認識。屬血氣之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斷地往一場自己無法撲滅的火上澆水。他已經屈服於撒但的試探,成為撒但的奴僕。當撒但在樂園中試探亞當和夏娃時,牠試圖讓他們相信,人的自我意識是終極的,而不是衍生的、依賴上帝的。牠彷彿在論證,自我意識的本質就是使自己成為一切謂詞(all predication)的最終參照點。他彷彿在論證,上帝無法掌管時間進程中可能出現的一切。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在論證,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識都必須假設自身的終極性,因此也必須承認其自身的局限性,即許多事情的發生根本無法控制。因此,撒但彷彿在論證,人對時間以及時間在歷史中的產物的意識,即便是能夠理解的,也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上帝而存在。
然而,羅馬主義和福音派並不將人這種對自主性或終極性的假設歸因於罪。他們認為,人理應如此看待自己以及自己與時間中事物的關係。因此,他們對保羅關於罪對人的詮釋活動之影響的教導,做了不公正的處理。正如他們實際上否認人最初不僅具備領悟真理的能力,而且實際上擁有真理,他們也實際上否認了屬血氣之人會壓制真理。
羅馬主義和福音派都對挑戰那些「哲學家」興趣缺缺,這並不奇怪,因為正如加爾文所說,當這些哲學家在詮釋人的意識時,並未意識到墮落前後,人對真理的態度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他們並未仔細區分屬血氣之人對自己的理解和聖經對他的理解有何不同。然而,對於接觸點的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在沒有意識到這種區別的情況下,就向屬血氣之人發出呼籲,我們實際上就等於承認屬血氣之人對自己的評估是正確的。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堅持認為他迫切需要信息。我們甚至可以承認他在道德上是敗壞的。但是,在此基礎上,我們不能承認的一件事是,他聲稱自己能夠以本質上正確的方式詮釋至少某些經驗領域,這種聲稱是錯誤的。那麼,我們就無法質疑他最基本的認識論假設,即他的自我意識和時間意識是自明的(self-explanatory)。我們不能質疑他以完全內在主義的範疇(immanentistic categories)詮釋其所有經驗的權利。而一切都取決於此。因為如果我們首先承認屬血氣之人將自己作為任何維度詮釋中終極參照點之假設具有正當性,我們就不能否認他有權以自然主義的術語來詮釋基督教本身。
因此,福音的接觸點必須在屬血氣之人的身上尋找。在他的內心深處,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上帝的受造物,要對上帝負責。每個人在骨子裏都知道自己是背約之徒(covenant-breaker)。但每個人的言行舉止都彷彿並非如此。這一點在他面前是絕對不能提起的。一個人可能患有裏面的癌症。但他絕不願別人在他面前提起。他會承認自己身體不適,只要藥物不被誤認是針對癌症診斷而開立的,他就會接受。一個好醫生在這方面會迎合他嗎?當然不會。他會告訴病人,他有活下去的指望,但前提是必須立即進行裏面的手術。罪人也是如此。他活著,卻是以背約之徒的身份活著。然而,他對一切事物的詮釋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這並不是事實。羅馬主義和福音派由於未能完全訴諸人內心深處那被每個人壓制的意識,實際上就等於認可了屬血氣之人對自己看法的正當性。他們並不試圖攻破那座屬血氣之人總是逃往、總是據守的最後營壘(譯按:參林前十4-5)。他們只割除表面的雜草,卻不將這些雜草連根拔起,因為害怕農作物無法生長。
另一方面,真正符合聖經的觀點,則以原子能和火焰噴射器之力,徹底顛覆屬血氣之人關於自己看法的預設。它無懼於失去接觸點,而是選擇將雜草連根拔除,而非僅僅在表面割除雜草。它確定每個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上帝的律法已深深印在他們身上,因此,接觸點必然存在。唯獨基於這個事實,他可以安心地面對接觸點的問題。29 因著這一事實,使人始終可以被上帝接近。這一事實向我們保證,每個人,若要成為真正的人,就必然已經接觸到真理。他與真理的接觸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他耗費大量精力,徒勞地試圖向自己隱瞞這一事實。而他向自己隱瞞這一事實的努力,註定是自我挫敗的。
唯有如此,在人的神性意識中找到接觸點——這種神性意識潛藏在他「把自我意識視為終極」這個概念之下——我們才能既忠於聖經,又能有效地與屬血氣之人進行推理的對話。人,明明認識上帝,卻不願記念上帝。
注:
1. The rest of the material of this chapter is taken from the Syllabus on Christian Apologetics.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44, p. 21.
3. Warfield: Plan of Salvation, Grand Rapids, 1935, p. 111.
4.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9, p. 90.
5. Systematic Theology, 2, 103.
6. Idem, p. 105.
7. Institutes, Bk. 1, Chap. 15, Sec. 8.
8. Idem, 1, 15, 6.
9. Idem, 1, 4, 1.
10. Systematic Theology, 2, 99.
11. Idem, p. 100.
12. Idem, p. 101.
13. Idem, p. 244.
14. Vol. III. P. 16.
15. Idem, p. 35.
16. Idem, p. 36.
17. Ibid.
18. Warfield: Plan of Salvation, Grand Rapids, 1935, p. 111.
19. Ibid.
20. The Syllabus on Evidences takes up the position of Butler in detail.
21. Studies in Theology, New York, 1932, p. 9.
22. Idem. p.43.
23. Idem. p.45.
24. Systematic Theology, 1, 49.
25. Idem. p.50-53.
26. Institutes, 1. 15.8.
27. Kampen, 1914, p. 165.
28. Studies in Theology, p. 110.
29. 這裏,如同在本章中,論點並非我們應該從「絕對倫理對立」(absolute ethical antithesis)的概念出發來分析屬血氣之人的知識,而是應該像加爾文一樣從神性意識的角度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