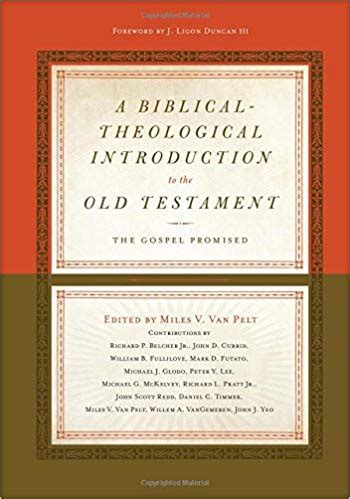
第二章 出埃及記
摘自《舊約聖經神學導論》
約翰·科瑞德
簡介
《創世記》以希伯來文單詞מִצְרַ֫יִםבּ結尾,它的字面意思是「在埃及」。這當然為《出埃及記》提供了背景,而事實上,它也是一個預兆性的評註,因為在《出埃及記》的開頭,從《創世記》結尾起,希伯來人就在埃及已為奴了四百年。這種為奴的狀況應驗了《創世記》十五章中上帝向亞伯拉罕說出的預言:「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創十五13)然而,在立約儀式的過程中,上帝又賜了另一個應許給亞伯拉罕:「並且他們所要服侍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創十五1)《出埃及記》的中心信息是,上帝將亞伯拉罕的後裔從埃及地為奴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從而信守了應許。
《出埃及記》的希伯來文標題(ואלה שמות)來自經文中的兩個希伯來文單詞,譯作「[然後]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面……」我們要注意,經文是以「然後」(and)這個詞開頭的(希伯來文中的連詞waw),許多現代譯本都省略了這個連詞。然而,這個連詞將《出埃及記》的故事和之前《創世記》的敘述材料連結在一起,表明了敘述自然而然的發展流程,並突出了這是一個發展中的故事。「[然後]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面……」也是《創世記》中家譜的常見引導性慣用語。這個重複的表述將兩經卷連結在一起,表明了《出埃及記》的作者相當熟悉《創世記》——這個事實在《出埃及記》被反覆強調。
《出埃及記》的英文標題Exodus源自一個希臘文單詞,意思是「出去」;《新約》用這個單詞指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希伯來書》十一章22節說:「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這個標題英文標題源自於希伯來文聖經的古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該譯本從經文中選用了這個主導詞,作為整部經卷信息的焦點。的確,《出埃及記》的大部分篇幅都敘述了以色列藉上帝之手從埃及地離開或「出去」。
背景問題
學者們時常質疑《出埃及記》的作者對埃及究竟瞭解多少。例如,唐納德·雷德福德(Donald Redford)總結道:「《出埃及記》的敘述中幾乎沒有多少埃及的色彩,幾乎只有表面上與埃及相關;但埃及學家很快就會發現這裏的敘述具有時代錯誤。」1 這種視角並不新鮮。英國的埃及學家T·艾瑞克·皮特(T. Eric Peet)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評論道:「讓埃及學家感到驚訝的一個主要事實是,[帶有埃及色彩的聖經敘述中]完全沒有提到希克索斯王朝(Hyksos),甚至沒有提到任何具體的王朝。這裏的常識完全是模糊的。」2 這種質疑在聖經研究和埃及學領域都是一種佔主導地位的詮釋方式。
近年來的一些著作試圖證明《出埃及記》的作者其實很熟悉埃及的習俗和信仰。3 例如,《出埃及記》七章8至13節中「杖變蛇」對抗:「充滿了埃及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元素。只有十分通曉埃及傳統的作者才可能描繪出這一幕具有濃厚埃及特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4 《出埃及記》中的許多故事都巧妙地批判了埃及的風俗習慣和信仰。例如,像「紅海分開」這樣的片段就是在諷刺性地批判埃及文學作品中類似的敘述。
聖經作者通常會用一些類似的慣用語表達來貶低埃及。例如,聖經描述主耶和華用「大能的手」羞辱和消滅法老和埃及(出三19-20,六1,七4,十五16等)。這是一種諷刺,因為古埃及文獻典型地用法老「大能的手」這種措辭來說明法老的權力;法老「擁有大能的手」,「以大能的手消滅仇敵。」5 在有關「十災」的敘述中,上帝預言了將有一場重大的冰雹降在埃及,「自從埃及開國以來,沒有這樣的冰雹」(出九18)。這種宣佈反映了當時埃及一種常見的表達。法老們,比如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is III),會宣佈自己做的某件事「比自從埃及開國以來的任何事都要偉大」。6 上帝用了同樣的慣用語來證明祂對法老、埃及、以及自然現象享有的權力。
聖經作者在《出埃及記》中還用了一些古埃及語詞彙。7 有時,作者將一些古埃及詞語用作雙關語。例如,古埃及太陽上帝「拉」(Ra)的名字和希伯來的רע(ra)這個觀念(在希伯來文中意思是「惡/禍患」)就是明顯是雙關語;我們在《出埃及記》五章10節、十章1節、三十二章12和22節中以及摩西五經的其他一些地方都能看到明顯的暗指。作者用這種雙關語是為了諷刺埃及的主神。8 另一個有趣的雙關語涉及法老女兒為摩西起名字。當年幼的摩西被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時,摩西就做了「她的兒子」(出二10)。她給他起名「摩西」,這個名字來自於希伯來文動詞「拉出來」。然而,這個詞也是一個古埃及語單詞,意思是「某某的兒子」。古埃及人的名字通常用這個詞和其他詞合成一個詞;例如,埃及法老圖特摩斯(Thutmosis)的名字,字面意思是「圖特(Thut)的兒子」,而國王阿赫摩斯(Ahmosis)是「阿赫(Ah)的兒子」。「摩西」這個名字沒有明確的所指對象,因此意思就是「某某的兒子」。這或許是聖經作者用來強調這一點的雙關語:摩西不是埃及或埃及諸神的兒子,而是以色列和主耶和華的兒子。摩西後來和埃及脫離了關係(見來十一24-25)。
結構與概述
關於《出埃及記》的結構,學術上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9 然而,這部經卷似乎是雙聯畫式的(diptych),也就是說,兩個畫板或基本部分拼接在一起。第一至十八章講述了以色列先是在埃及,然後逃到了曠野的西奈山;第十九至四十章講述了上帝在西奈山賜下律法。這兩部分雖在歷史和時序上被拼接在了一起,它們卻在許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第一至十八章主要是歷史敘事,而第十九至四十章則主要談論立法。儘管第二部分中顯然也有歷史敘事,但上帝對律法事務的啓示佔據了主導地位。其次,兩部分之間有一個重要的神學轉變。正如道格拉斯·斯圖亞特(Douglas Stuart)所說:「在埃及,以色列是法老的奴僕;在西奈山上,他們成了上帝的僕人。」10 因此,《出埃及記》的結構很淺顯易懂:第一部分解釋了以色列如何去往西奈山,第二部分講述了在西奈山發生了什麼。
這幅「雙聯畫」的第一部分有自身的結構,而這一結構表明了這部分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文學片段。這個結構將摩西的早年生活體現為出埃及事件的一個雛形和縮影。也就是說,摩西生平中在埃及、米甸以及西奈山的這些片段說明並預示正在形成的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中一些突出事件。我們可思考一下表5中的幾點相似性。
| 摩西 | 以色列 |
| 1. 《出埃及記》二章1至2節:摩西作為一個奴隸出生在埃及;他是在壓迫和逼迫之下出生的;法老企圖殺死他(出1:15-22)。 | 1. 《出埃及記》一章8至22節:以色列人在埃及生來為奴;他們活在殘酷的奴役之下;法老企圖殺死他們的所有男嬰。 |
| 2. 《出埃及記》二章3至1節:摩西經歷了水的考驗,最終得救。 | 2. 《出埃及記》十四章1節至十五章21節:以色列在紅海經歷了水的考驗,最終得救。 |
| 3. 《出埃及記》二章11節至22節:摩西逃往米甸/西奈。 | 3. 《出埃及記》十六章1節至十八章27節:以色列逃往米甸/西奈。 |
| 4. 《出埃及記》三章1至22:上帝在西奈山上向摩西顯現。 | 4. 《出埃及記》十九章1節至四十章38節:上帝在西奈山上顯現。 |
| 5. 《出埃及記》四章1至17節:摩西猶豫遲疑,但上帝是信實。 | 5. 托拉(Torah)餘下的部分:以色列作出了不忠的回應,但上帝是信實的。 |
表5 11
兩份敘述不僅在許多方面是很相似,發展模式也一樣。甚至兩份敘述中的措辭也在一定程度上很相似。例如在表5中摩西一欄的第三點相似性那裏(出二11-22),葉忒羅的女兒們被牧羊人欺壓、趕走,無法去飲她們父親的群羊。摩西的反應是,作為一名拯救者介入,拯救她們脫離了苛待。第17節中表示「幫助/拯救」的希伯來文單詞(ישע)是被用來描述以色列被拯救逃離埃及的一個主要單詞(例如出十四30)。在《出埃及記》二章19節中,葉忒羅的女兒們說:「有一個埃及人救我們脫離牧羊人的手。」這句話幾乎逐字重複了葉忒羅後來說的話:「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救了你們脫離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出十八10)。這種語言上的密切關係表明了摩西救葉忒羅女兒們的片段,是主耶和華(透過摩西)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樣板。
信息與神學
作為引導主題的出埃及事件
出埃及事件代表著以色列的一個決定性時刻,無論就其歷史還是就其將來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舊約》中一些後來的先知將出埃及事件描述為又一次救贖作為的樣板,就是以色列從巴比倫被擄中歸回的樣板。例如,主前八世紀的先知以賽亞預言以色列和猶大將被毀滅,但有朝一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賽十一11;參亞十9-11)以色列將逃離奴役並回到應許之地,正如他們在第一次逃離時[出埃及]那樣:「為主餘剩的百姓,就是從亞述剩下回來的,必有一條大道,如當日以色列從埃及地上來一樣。」(賽十一16)
《以斯拉記》也提到了上帝百姓從巴比倫歸回和出埃及事件有一些相似之處。換言之,《以斯拉記》敘述的以色列民從巴比倫的兩次歸回以出埃及事件為範本;它們重複了最初的那次逃離和歸回。《以斯拉記》的開篇講述第一次歸回(主前538年);在此次回歸中,百姓們定居在應許之地(拉二70)。定居後,百姓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建築祭壇,開始在其上早晚獻祭,正如摩西曾命令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所做的一樣(拉三2-3;參出廿九38-39)。隨後,百姓們在應許之地慶祝了他們的頭一個節日,就是住棚節(拉三4)。這個被稱作住棚節的節日是為了紀念以色列人在從埃及出逃的危險當中,上帝保守了他們(利廿三42-43)。它突出上帝百姓回歸應許之地時,上帝對他們的看顧,而曾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今回歸後慶祝一番,也是完全恰當的舉動。從《以斯拉記》三章起,以色列人便開始在耶路撒冷為上帝重建聖殿,正如希伯來人出埃及並在迦南地定居之後所做的。聖殿完工時,他們為上帝的殿舉行了奉獻典禮,與《列王紀上》八章中所羅門舉行奉獻典禮的方式十分相似。最後,百姓們慶祝了逾越節。這是紀念以色列從埃及被上帝拯救出來的節日,如今被應用於從巴比倫回歸的餘民身上(拉六19-22)。
其他一些聖著也識別出這兩次離開事件之間的關係。偽經《以斯得拉二書》或稱《以斯拉續篇下卷》(Second Esdras 或2 Ezra)確定祭司以斯拉是第二摩西。它宣稱以斯拉是新的立法者(十四19-48),他用四十天重寫或編輯了聖經(參見摩西在西奈山上四十天)。儘管這份聖著不被列入正典,但它對以斯拉和摩西關係的解釋很有洞見。《以斯拉記》七章10節說:「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這句話似乎基於《申命記》四章5至6節:描述摩西做了同樣的事。另外,在《以斯拉記》七章25節,以斯拉任命一些審判官去監督律法在各地的執行,正如摩西在米甸所做的(出十八21-22)。
從巴比倫的歸回被理解為又一次「出埃及」,而以斯拉被視為第二摩西。不過按這種理解,這次歸回就只是一種回聲,而沒有任何提升和強化。這次歸回只是又一次「出埃及」,而非更重大的「出埃及」。它缺少了第一次「出埃及」的救贖份量。然而在聖經隨後的部分,這次出走歸回的確指向了一次更大的拯救。在《新約》中,《馬太福音》的結構正是基於出埃及事件的樣板。12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表6中的相似點。
| 出埃及記 | 馬太福音 |
| 1. 以家譜開頭(1:1-5) | 1. 以家譜開頭(1:1-17) |
| 2. 拯救者的出生(2:1-10) | 2. 拯救者的出生(1:18-25) |
| 3. 法老逼迫以色列(1:8-14,2:11) | 3. 希律王壓迫猶太人(2:1-12) |
| 4. 摩西從埃及出逃(2:15) | 4. 耶穌逃往埃及(2:13-15) |
| 5. 法老殺男嬰(1:15-22) | 5. 希律王殺男童(2:16-18) |
| 6. 以色列過紅海(14:1-31) | 6. 耶穌受洗(3:13-17) |
| 7. 以色列在曠野受試探四十年(民數記) | 7.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四十天(4:1-11) |
| 8. 西奈山賜下律法(出20:1及隨後幾節) | 8. 登山寶訓(5:1~7:29) |
表6
出埃及事件的高潮是逾越節的設立:上帝在此時審判了埃及,拯救了以色列(出十一1~十二51)。這一高潮指向了《新約》中基督一生的巔峰事件:正如《舊約》中逾越節的羔羊,耶穌流寶血遮蓋了自己百姓的罪,讓給上帝的烈怒不要臨到他們(約一29;彼前一19)。使徒保羅宣告:「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五7)。耶穌是逾越節的羔羊,祂流寶血替代自己的百姓,使他們免於上帝的忿怒和審判。也就是說,「正如以色列被逾越節羔羊的血遮蓋,新以色列被彌賽亞的血遮蓋。」13
古代近東文學與《出埃及記》的敘事
《出埃及記》中的許多事件,尤其是摩西生平,都反映了古代近東地區一些常見的情節主題(plot-motif)。14 例如,在該地區許多不同文化中(包括埃及)都發現的一個主題就是有關某嬰孩出生的敘事:新生的嬰孩面臨著被殺害的威脅,卻活了下來,並成長為自己百姓的領袖/拯救者。在古代近東地區,這一情節主題是古老而司空見慣的。它出現在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赫梯,而首次出現則是在主前第三個千年的末尾。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故事與《出埃及記》二章1至10節所記錄的有關摩西出生的敘述有一些醒目的相似之處。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係?「二者是否相互獨立?是否聖經作者只是從周圍文化那裏借鑒了這段著名的文學描述,並且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它?這段經文究竟是傳說、神話還是歷史?」15
許多學者都相信,有關摩西出生的敘述顯然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薩爾貢傳說》(Legend of Sargon)有關。16 這兩份敘述雖有一些相似點,但相似點似乎都十分籠統和微弱。而即便要尋找關聯,我們也應當尋找和埃及文學著作的關聯,因為聖經中摩西出生的故事發生在埃及。蓋里·倫茨堡(Gary Rendsburg)正確地評論道:「聖經文學的本質暗示出,我們若要解釋發生在埃及的某個故事當中的某個特徵,不應當查看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學著作,而應當查看埃及的文學著作。」17 事實上,考古學家們在埃及發現了一份文獻,被稱作《何露斯的神話》(Myth of Horus),當中有「被暴露的嬰孩」這個情節主題。18
這份文獻講述了一個發生在諸神領域的故事。混沌和戰爭之神塞斯(Seth)殺死了司陰府之神帝奧西裏斯(Osiris)。奧西里斯的妻子伊希斯(Isis)讓奧西裏斯復活並從他懷了孕。她在「凱姆來司的沼澤地中」生下了一個名叫何露斯(Horus)的兒子。現在的處境很危險,因為如果塞斯如果聽說何露斯出生了,就會殺掉這個嬰孩。伊希斯和孩子成功地逃離了塞斯,躲藏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沼澤地裏。在那裏,伊希斯把何露斯放在一個蒲草箱裏,藏在了厚厚的蒲草叢中。19 塞斯企圖殺死還是嬰孩的何露斯,但何露斯活了下來,而文獻的結尾講述了何露斯長大成人,足以打敗塞斯並成為眾神的領袖。
聖經有關摩西出生的敘述與何露斯出生的故事很相似。表7展示了主要的相似點。
| 何露斯的出生 | 摩西的出生 |
| 1. 新生兒遇到很大的危險:塞斯企圖殺死他。 | 1. 新生兒遇到很大的危險:法老企圖殺死他(出一15-22) |
| 2. 母親的角色得到了強調:伊希斯保護了新生兒。 | 2. 母親的角色得到了強調:約基別保護了新生兒(出二2)。 |
| 3. 伊希斯將嬰孩放在一個蒲草箱裏,把他藏在蒲草叢中。 | 3. 約基別將摩西放在一個蒲草箱裏,把他藏在尼羅河邊的蘆荻中(出二3)。 |
| 4. 家族中的另一位女性守護著嬰孩:何露斯的姨母奈夫提斯(Nephthys) | 4. 家族中的另一位女性守護著嬰孩: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出二4)。 |
| 5. 伊希斯乳養嬰孩。 | 5. 約基別乳養嬰孩(出二7-9)。 |
| 6. 月神透特(Thoth)幫助伊希斯和何露斯。 | 6. 主耶和華前來幫助全以色列(出二23-25)。 |
| 7. 何露斯成長為埃及第一等級的神,化身為法老。 | 7. 摩西成長為一名領袖,拯救以色列脫離法老的手。 |
表7 20
有關摩西出生的敘述反映了埃及的習俗和信仰,甚至包含了一些埃及語詞彙。例如,約基別將摩西放在「一個蒲草箱」裏(出二3),這是埃及人對紙莎草器皿的稱呼。這段敘述簡直到處都有埃及的痕跡。
倫茨堡正確地說道:「所有證據都是清楚的:毫不意外,發生在埃及的一個聖經故事相似於埃及的一個著名的、流行的神話。」21 兩個故事之間的關聯無可否認,但問題是,它們之間是如何相關聯的?聖經作者為何有意讓二者相似?他或許是為了引發爭辯,而有意從一個著名的埃及神話中運用了這種相似。在埃及不過是神話的故事,卻真實發生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就是說,聖經作者採用了一個著名的異教神話,把它翻轉過來,為的是要奚落和嘲諷埃及,然後突出聖經故事的真實性。
另一個例子是《出埃及記》十四章13至31節敘述的紅海的水被分開。古埃及人也有一個這樣的故事,講述了一個祭司如何將大水分開。這個故事是韋斯加紙莎草文獻(Westcar Papyrus)的一部分,描述了古埃及第三和第四王朝(約主前2649-2465年)幾位術士施展的一系列魔法。22但這份文獻是後來才被寫下的,或許早至主前二十世紀。無論哪種情況,都比出埃及事件早了數百年。紙莎草文獻講述的故事是,一位感到無聊的法老斯尼夫魯(Snofru)召見了一位叫做達加達莫卡(Djadjaemonkh)大祭司,想辦法找些樂子。達加達莫卡建議法老去湖上坐船遊玩,讓許多美艷的裸體婦人划船。法老同意了,玩得很開心,直到其中一個婦人身上的魚形護身符掉進了湖裏。這位婦人不願意接受任何替代品,於是法老叫達加達莫卡施法術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位祭司念了一些咒語,於是湖水向兩邊分開了,一邊堆到了另一邊上面。他在一塊陶瓷碎片上發現了護身符,將它還給了婦人。最後,他又施了一些法術,湖水恢復了原樣。
聖經中有關紅海分開的敘述讓我們想到這個埃及故事。但聖經作者是出於什麼目的要讓這兩個故事相似呢?他或許是在批判這位埃及術士和他的法術。埃及的大祭司或許曾分開湖水以便取回一個貴重的護身符,但上帝透過摩西分開了整個紅海,以便拯救自己的百姓脫離埃及的奴役。誰展示了更大的能力呢?
有關十災的敘述
作為嘲諷的十災
上帝對埃及的審判以及希伯來人逃離埃及的方式是按照《出埃及記》七章8節至十二章51節中的十災構建起來的。十災敘述的中心是一場競賽,但這根本上不是摩西和法老或摩西和埃及術士們之間的競賽,就此而論,也不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競賽。這是一場屬天的戰鬥,也就是說,是希伯來人的上帝和埃及諸神之間的戰爭。聖經作者準確地洞察到了這件事是神學事件。這裏問題是,誰是真神?誰掌管著整個宇宙的運行?誰的旨意要在天上地下成就?
支持這種觀點的教導是:十災中的每一災都是上帝針對某一具體埃及神明的。23 我們能以這種方式來解釋十災中的每一災。例如,第一災(出七15-25)顯然針對的是尼羅河。埃及人相信尼羅河濫時會變成一個神明,化身為哈皮神(Hapi)。在藝術描繪中,埃及人將哈皮神描繪成一個長鬍鬚的男人,有著女人的乳房和一個垂下來的大肚子(或許是懷孕的標誌)。這種雌雄同體的描繪反映了「多產」這個觀念。古埃及人的確相信尼羅河透過定期濫維繫著埃及,這種信念為許多現存的文獻所證實。24 因此,當上帝將尼羅河水變作血時,是在直接攻擊這位神明;多產之神哈皮不再能供應埃及人民的所需。這一災嘲諷了埃及的神,因為真正的維繫只來自於有主權的宇宙之主,而非來自一個假神。
這裏我們還能再舉一個例子。古埃及人認為太陽化身為人的阿蒙拉(Amon-Ra)是主神。他們相信當阿蒙拉從東邊升起時,便象徵著新生命和重生。事實上,許多文獻都將阿蒙拉描繪為創造之神。25 然而,當這個神明從西邊落下時,他就成了對立的一面,代表著死亡和陰間。因此,當上帝在第九災中定下旨意時,太陽就按祂的旨意變黑暗了(出十21-29),而阿蒙拉無法作為生命的象徵來照耀他的子民。相反,他象徵著審判、死亡和無望。
言歸正傳,上帝在埃及降下十災來拯救自己的百姓,這是對埃及諸神的直接攻擊。《舊約》有這樣的理解:「逾越節的次日,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無懼地出去。那時埃及人正葬埋他們的長子,就是耶和華在他們中間所擊殺的,耶和華也敗壞他們的神。」(民卅三3b-4)對埃及多神教的嘲諷是十災敘述的中心(參耶四十六25)。
作為創造之毀滅(創世論)的十災
當讀者思考諸如十災這樣的敘述時,重要的是要根據上帝啓示所具有的逐漸展開的本質,來查看敘述片段的語境。正如探討《創世記》那章所提到的,我們必須關注創世論(protology)(「對起初之事的研究」)。《出埃及記》的作者很熟悉《創世記》,他是基於《創世記》中創造敘述的神學和用語,構建了《出埃及記》一至十五章的敘述。26 也就是說,有關以色列被救出埃及和過紅海的敘述反映了起初創造的敘述。我們能在許多方面看到這種關聯。首先,在《出埃及記》開頭一段,作者說:「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出一7)這句為整部《出埃及記》奠定了背景的陳述,用了五個動詞,與描述創造的用語、尤其是《創世記》一章28節中創造命令的用語十分相似。作者有意讓這段敘述與《創世記》相似,是為了強調希伯來人在埃及時履行了這條命令,以色列是又一個亞當。因此,《出埃及記》的作者將這段敘述打造成一個有關再創造的敘述。
其次,「摩西在尼羅河中經歷水的考驗」這個片段與《創世記》六至八章中有關挪亞在大洪水中的敘述很相似。摩西出生後,他母親不能再從當權者面前藏住他了,就把他放進了一個「箱子」(ּתבה,出二3)。這個希伯來文單詞在有關挪亞的敘述中被用到了24次,指的是「方舟」。此外,摩西的母親還以「石漆和石油」(出二3)蓋住了箱子,和挪亞對方舟所做的一樣(創六14)。正如我們在研究《創世記》時所看到的,有關挪亞的敘述表明了一個再創造事件,在當中上帝向挪亞重申了生養眾多的命令,而挪亞被塑造成了又一個亞當(創九1)。《出埃及記》一章中希伯來人正在履行的正是這個命令,因為他們在埃及生養眾多。聖經作者正在將以色列被拯救出埃及描述為一次再創造。
再次,在紅海發生的偉大拯救事件是以《創世記》中的創世敘述為樣板而構建的。正如沃倫·蓋奇(Warren Gage)的評論:「以色列在紅海經歷的救贖性創造敘述,遵照了起初創世的敘述模式:核心就是上帝的臨在把光帶入了黑暗(出十三21,參見創世的頭一日),水被分開(出十四21,參見創世的第二日),旱地露出來(出十四29,參見創世的第三日)。」27 聖經敘述教導了,紅海的分開——以及就此而論的整個出埃及事件——是又一次創造。這是又一次勝過了混沌,又一次勝過了深水,也是將以色列民創造成上帝的聖約百姓。
聖經研究文獻廣泛提到了這些創世元素。但鮮少提到的是,與埃及地相關的十災敘述諷刺地反轉了創世敘述。28 也就是說,上帝透過降下十災而攻擊並打亂了《創世記》一章中創世敘述的主要元素,正如表8所顯示的。
| 創世六日 | 描述 | 埃及的十災 | 描述 |
| 頭一日:《創世記》1:3-5 | 光中黑暗中被創造出來 | 第九災:《出埃及記》10:21-29 | 黑暗勝過了光 |
| 第二日:《創世記》1:6-8 | 水被整理分開 | 第一災:《出埃及記》7:15-25 | 通過水變血而產生了混亂 |
| 第三日:《創世記》1:9-13 | 旱地露出,植物長出來 | 第七至八災:《出埃及記》9:13-10:20 | 植物被毀滅 |
| 第四日:《創世記》1:14-19 | 眾光體的被造 | 第九災:《出埃及記》10:21-29 | 眾光體變黑暗 |
| 第五日:《創世記》1:20-23 | 鳥、魚、以及海洋動物的被造 | 第一至二災:《出埃及記》7:15~8:15 | 魚和青蛙死亡 |
| 第六日:《創世記》1:24-30 | 地上活物和人類的被造 | 第三至六災:《出埃及記》8:16-9:12 第十災:《出埃及記》11:1~12:51 | 昆蟲之災,人和動物身上生瘡;擊殺長子 |
表8 29
這種關聯證明了創造天地的主耶和華是在用十災變亂埃及的自然秩序。
幾個與十災相似的地方(末世論)
《出埃及記》中十災敘述開啓了一個在聖經從頭到尾不斷出現的主題。例如,我們在《撒母耳記上》四至七章有關約櫃的敘述中明顯可看到這種災禍模式。30 在此處敘述中,非利士人打敗了以色列人,搶走了約櫃。因此,約櫃作為戰利品被放在了外邦的土地上。這個事件的後果之一就是,上帝也像降災與埃及那樣降災與非利士人,從而確保約櫃能被奪回來(見《撒母耳記上》六章4節,「災」這個詞出現在了此處)。兩處敘述之間有明確的相似性。
兩個事件之間的相似性在語言和神學層面都很明顯。從語言的角度看,兩個故事用到的許多重要詞彙是一樣的。這一現象在《撒母耳記上》五章6節至六章4節中尤為突出。例如,當上帝降下生痔瘡的災禍給非利士人時,文中用到了「攻擊/擊打」一詞(撒上五6,9,12中的נכה),這個動詞也被頻繁用於出埃及敘述中(例如,出九15)。《撒母耳記上》六章4節中表示「災」的單詞,雖然在希伯來詞彙中並不十分常見,卻出現在了《出埃及記》九章4節,作為上帝在埃及所降一切災禍的總結性詞語。希伯來文中表示「驚慌」的單詞在《舊約》中同樣不常見,卻在有關約櫃的片段中出現了兩次(撒上五9,11),並出現在了《出埃及記》十四章24節:上帝使埃及的軍兵大大混亂。在《撒母耳記上》五章7節,亞實突人說上帝的手「重重」(קשה)加在他們身上。這也是出埃及敘述中的一個重要詞語(出六9,十三15),它也被用來作為一個標準化的詞語來指法老的心硬(例如,出七3)。
《撒母耳記上》五章10至11節,當以革倫人對臨到自己的災禍作出反應時,有一個不尋常的表述出現過兩次。希伯來原文直譯過來就是「殺掉我和我的民」。這個表述的不尋常之處在於,以革倫人(複數)說話時用到了「我」和「我的」這兩個單數代詞。一些人認為可能是有一個人代表全體以革倫人發言,或是單數表示集體的意思。然而我們應注意到,「我和我的民」或「法老和他的民」這種表述在出埃及故事中出現了20餘次。例如,《出埃及記》八章8節引用了法老的話:「請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離開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因此,《撒母耳記上》五章10至11節的文字似乎是指向了出埃及的敘述,並表明災禍模式是約櫃篇章的基礎。
《撒母耳記上》的作者識別出了這種模式,他也引用了非利士人的話來證實這種模式。非利士人的祭司和占卜的對非利士百姓說:「你們為何硬著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樣呢?上帝在埃及人中間行奇事,埃及人豈不釋放以色列人,他們就去了嗎?」(撒上六6)即便遭遇災禍時,非利士人也表現出了這種相似性,因為他們哀嘆道:「我們有禍了!誰能救我們脫離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從前在曠野用各樣災殃擊打埃及人的,就是這些神。」(撒上四8)雖然非利士人對希伯來人的一神論很困惑,但他們正確地看到了埃及的災禍模式正發生在他們的處境中。
《出埃及記》中十災敘述的主題在《啓示錄》中逐漸加強;在《啓示錄》中,災禍將在末時擊打撒但的追隨者們(參啓16)。也就是說,十災的敘述是一個樣板,展示了某一天將臨到所有不信之人的審判。例如,《啓示錄》透過盛上帝大怒的第二和第三碗重複了發生在埃及的第一災,描述如下:「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裏,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裏,水就變成血了。」(啓十六3-4)這些描述和《出埃及記》中那些敘述的相似性是顯然易見的。使徒約翰還引用了另外一些災,比如第七災冰雹災:「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上帝。」(啓十六21)《啓示錄》中冰雹的規模強調了末世災禍的強度和嚴重程度;這災比埃及的災要大得多。事實上,臨到埃及人的災禍僅僅是末世最後審判的預嘗。也就是說,《出埃及記》中的十災將再現於《啓示錄》,它們也預示了在末日將要臨到上帝仇敵的是什麼。
宇宙的秩序:瑪阿特
古埃及人相信一種被稱作瑪阿特(Ma’at)的宇宙秩序。瑪阿特可被定義為:「和諧、秩序、穩定、安穩的宇宙力量……以及被造現象界的有組織的特質。」31 在古埃及人看來,這種力量是首次創造的結果,是混沌的反面;它將宇宙結合在一起。在古埃及,維持瑪阿特是法老的責任,因為法老被視為瑪阿特的精髓和本質。事實上,新法老登基時,便擔負起責任來重建和重新支持瑪阿特。他要透過自己的統治和領土來維持創造的秩序。按照西里爾·奧爾雷德(Cyril Aldred)的說法,「法老建立瑪阿特的方式是他的『有權威的言語』和他的『認識』。」32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恢復並為維持這種和諧是埃及法老必須做的,預期著法老的身份的確是太陽上帝的兒子,也是被奉為上帝的統治者。」33 當主耶和華以十災攻擊埃及時,祂正在讓埃及陷入混亂。祂不僅是在反轉創造,還在毀掉埃及的創造。祂是在將宇宙秩序(瑪阿特)變得無序或一片混亂。這最終是對法老及其自誇的能力和主權的攻擊。法老能經受住自己的控制領域被入侵嗎?他不能,這一點突出了《出埃及記》尤其是十災敘述的一個主要主題:「透過表明法老在聖約之上帝主耶和華面前毫無能力來挑戰了這一基本觀念[瑪阿特]。」(出十二12)34 瑪阿特這個埃及觀念的毀滅證明,唯有主耶和華才掌控著宇宙;唯有祂是有主權的。
法老的心剛硬
《出埃及記》中另一個強調上帝主權的主題就是法老的心剛硬。這一中心主題在雙聯畫的前半部分,在第一至十八章中從頭到尾都有出現。它是一個主要主題,強調了上帝在埃及和法老之間的整場衝突。這個概念的首次出現是在《出埃及記》四章21節;上帝說了一番有關法老的話:「但我要使他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在整個敘述中,聖經作者不斷說明是主耶和華讓法老的心剛硬(出七3,九12,十1、20、27,十四4、8)。整段話從頭到尾都用到了三個希伯來文單詞來指出法老的心是剛硬的狀態;四章21節用來表示「剛硬」的那個詞帶有這種觀點:法老始終強硬而決絕地定意不屈服於主耶和華的要求,就是讓百姓離開。35 上帝是法老心剛硬的原因。
埃及背景闡明了這個主題有著多麼深層次的意義。古埃及文獻說,或許是人身上最重要的部分。法老的心尤其重要,因為埃及人相信法老的心在歷史和社會中具有主權式的全然控制力。埃及人進一步認為,太陽神「拉」和神明何露斯的心對萬物享有終極主權。36 由於他們認為法老是這兩位神明的化身,因此認為法老的心也同樣對現存的萬物享有主權。「主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證明了只有希伯來人的上帝才是真正宇宙主宰者。主耶和華甚至控制著法老的心⸺這是整部《出埃及記》的一個中心事實。這段敘述很好地例證了《箴言》作者的話:「主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廿一1)
在《出埃及記》七章14節,主耶和華說:「法老心裏固執/心剛硬。」這裏被用來表達「剛硬」的單詞,最基本的意思是「重」。古埃及信仰再次闡明了「法老的心很重」這個說法。37 在古埃及的新王國時期,就是出埃及事件發生的時期,埃及人相信人死後會在陰間面臨審判。死人的心臟(即:人的本質所在)會被放在真理的天平上過秤。天平的一端是心臟,另一端是代表真理和正義的羽毛。如果心臟因為罪行而重於這根羽毛,此人就被認為是不公不義的,就要被禁止進入埃及的來世:蘆葦之境(Field of Reeds)。
在出埃及的敘述中,「法老的心很重」這一判決表明了法老本質上是不義的,充滿了罪孽。考慮到古埃及人認為法老是無罪的,這一點尤為醒目。主耶和華對法老的直接攻擊,其實是在攻擊一個盛行的觀念:埃及國王的品性是純全無瑕疵的。
我們還應注意到,這段敘述有時也說是法老自己心剛硬(例如,出八15,32)。這個另外的原因或許說明了法老雖在上帝大能手的主權之下,但也要為自己的罪負責。這似乎正是使徒保羅對這件事下的結論(羅九14-24)。
律法
在《出埃及記》十九章的開頭,希伯來人到達了西奈山,在那裏上帝呼召摩西上山,與以色列民立約,並將自己的律法啓示給了他們。雙聯畫的後一半(出19~40章)主要是以立法文書的風格呈現的。它的確包含了多種文學形式,比如敘事(出卅二1-35)、應許(出廿三20-33)以及請求(出卅三12-23),但佔主導地位的文學風格是律法規定(jurisprudence)。我們將透過思考十誡來開始對希伯來律法的研究。
在思考希伯來律法以前,評論一下古埃及律法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後者為西奈山上的啓示提供了背景。在現存的上萬份古埃及文獻中,我們尚未發現任何一份是法典。諸如《西赫爾摩坡里斯通俗法典》(Demotic Legal Code of Hermopolis West)這樣的文獻並非編寫成法典的律法,而僅僅是生活和行為指南。38 事實上,法老是正義和律法的定義者和執行者。法老憑著自己的特權頒布新律法和更改舊律法。宣佈「這樣說」(出五10)的人是法老,而法老也能出爾反爾地更改律法,這就解釋了為何古埃及沒有眾所周知的、編寫成法典的律法。相比之下,主耶和華不是善變的,而是顯明了自己永不更改的律法。
十誡(出廿1-17)
上帝在西奈山上透過摩西來啓示律法,是從十誡開始的,因為十誡是基礎性、原則性的律法,以色列的所有其他律法都建立在此基礎上。十誡的結構和內容突出了對以色列會眾提出的十誡具有獨特的約束性本質。首先,我們應注意到,主耶和華直接向以色列啓示了這些律法,沒有以摩西或其他先知為媒介。上帝不僅說出了十誡,還用自己的手指將十誡寫在了兩塊石版上(出卅一18,卅二15-16)。其次,上帝賜下了十條誡命(或十句「話」),而這個數字在希伯來文化中似乎象徵著「完美」的概念⸺不允許有任何添加。經文進一步表明了,石版是兩面寫的,兩面都寫滿了,沒有添加的空間(卅二15)。最後,這些誡命被寫在石版上,永遠擦不掉。39
十誡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誡,宣佈並描述了我們對上帝的責任,第二部分是後六誡,描述了我們對人的責任。當一位律法師叫耶穌說出誡命中最大的一條,耶穌透過這樣總結十誡來作答:「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廿二37-40)這樣,耶穌明確支持並主張十誡對教會是繼續適用的、相關的。
在整個教會史上,許多人認為耶穌在《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登山寶訓中其實廢除了十誡中的一些。然而事實上,在那裏耶穌並非意圖要廢除十誡,而是要透過教導它恰當的解釋來強化它。例如,耶穌解釋道:「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太五21-22)這裏,耶穌是在解釋第六誡(出廿13)。當時的許多猶太人,包括法利賽人,都相信如果自己從未殺害任何人,也就完全守住了這條誡命。耶穌的看法卻相反:不僅我們的行為會定我們的罪,我們的心也是如此。因此,與法利賽人和其他人相比,耶穌在應用方面對十誡的理解要嚴格得多,也更容易定人的罪。《西敏信條》(1646年)對這一點進行了總結:「耶穌在福音中完全沒有廢掉[十誡],反而大大強化了這義務。」(19.5)
約書(出廿一1~廿三33)
約書中包含的各條律法不同於主耶和華在十誡中賜下的那些誡命。這些律法是摩西的手而非主耶和華的手寫下的(出廿四4)。這強調了在上帝將這律法賜給以色列百姓的過程中摩西的媒介作用(出廿一1),而上帝在啓示十誡時則是直接對百姓說話。在約書開頭的一句話中(出廿一1),這些律法被稱作「典章」(ּמִשְׁפָּטִים),這個詞指的是基於先前判例的判決。也就是說,十誡中的律法是原則性的、基礎性的、永久的,而約書中的律法涉及以色列百姓的具體社會和經濟環境。
例如,《出埃及記》二十二章1節說:「人若偷牛或羊,無論是宰了,是賣了,他就要以五牛賠一牛,四羊賠一羊。」這個法律判決就是將第八誡的原則「不可偷盜」(出廿15),應用於新興民族以色列的需求。十誡再次表明了基礎性的法律原則需要在任何時候和地方被應用於社會環境。約書則是衍生的,是將十誡的原則應用於以色列民族具體的社會環境,只在那個特定時代有效。
會幕的建造
《出埃及記》餘下部分中有很大篇幅都描述了主耶和華命令以色列民建造一個會幕,來作為以色列的敬拜中心。《出埃及記》二十五章1節至三十一章11節談到了上帝為這項建造工程下達的具體說明和指南,《出埃及記》三十五章1節至四十章38節則敘述了以色列人遵照上帝的命令,建造了會幕。會幕是一個可搬移的聖殿,以色列人走曠野時一直帶著它,它也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中心神殿,直到所羅門王統治時期希伯來人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聖殿。會幕本身的設計、樣式、材料都反映了以色列當時的遊牧狀況。40 希伯來文中表示「會幕」的詞和阿卡德語中表示「帳篷」的單詞有關,而這個詞在《舊約》中還有與「牧養」有關的用法。41
帳篷式神殿在古代很常見。在很漫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有它們的身影:從古代腓尼基人時代到現代伊斯蘭時代。42 在埃及,可搬移的神殿可追溯至主前2000至3000年,並且自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統治時期起(主前1290年-1224年)就有文字記錄予以證實。以色列人所用的建造方式實際上反映了「歷來已久的埃及技術」。43
金牛犢事件
儘管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與上帝立定了聖約(出廿四3-8),但他們很快就背棄了這約。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中,百姓叫亞倫為他們作神像,來為他們引路(出卅二1)。亞倫就依從了,從百姓那裏收集珠寶來鑄了一隻金牛犢(出卅二2-3)。百姓看見這金牛犢,就歡聲雷動:「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出卅二4)這一表達與耶和華有關自己對以色列所做之事的宣稱很相似(見出廿2;參利廿六13,詩八十一10)。亞倫回應了群眾的狂熱,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出卅二5)我們看見的正是一個有關「宗教融合」(syncretism)的片段⸺亞倫鑄造了一個古代近東地區常見的金屬偶像,宣稱它代表著以色列的上帝耶和華。這個事件的宗教融合本質體現在百姓要求得到多個神(第一節中表示「引路」的希伯來文動詞是第三人稱複數),而亞倫只鑄造了一個偶像。敬拜耶和華所包含的一個中心原則就是一神論,因此亞倫在這裏似乎持守住了這個原則。
亞倫和以色列百姓製作了主耶和華有形的像來拜,這違背了第二條誡命。亞倫甚至用雕刻的器具來製作了這個偶像。主耶和華之前甚至曾禁止以色列人用這類器具來為祂築壇(出廿25);為上帝製作一個有形的代表物,這個試探實在太大了。
這一事件是耶羅波安在但和伯特利樹立金牛犢崇拜(王上十二25-33)的歷史先例。我們尤其要注意,耶羅波安直接引用了西奈山悖逆以色列民的話;這位君王鑄造兩個金牛犢後,對眾民說:「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王上十二28)
古代近東地區的法典
摩西法典——首現於《出埃及記》隨後在整個摩西五經餘下部分得到了擴展——顯然不是古代近東地區已知的最早法典。美索不達米亞的一些法典比摩西律法要早好幾百年。一些重要的書寫成文的法典在主前兩千年初就出現了,比如《里辟伊士他法典》(Code of Lipit-Ishtar)和《肖納律法》(Laws of Shauna)。44 最著名的美索不達米亞法律是《漢謨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以其作者漢謨拉比命名,他是一位古巴比倫國王(主前1792年-1750年)。
時常有人認為摩西律法直接依賴於這些美索不達米亞法典。然而,並沒有直接的、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這種借用。兩種法典無疑體現出了一些相似之處,但「這可以透過犯罪種類和可能懲罰形式的有限性來解釋。」45 我們還應注意到,希伯來律法和美索不達米亞諸法典之間有一些巨大差異。例如,在《漢謨拉比法典》中,階層差別往往決定著如何應用律法,但摩西法典並沒有作這樣的區分——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此外,美索不達米亞諸法典總的來說遠遠沒有表現出對人命那麼大的重視;《舊約》律法卻不同,比如強調了照料孤兒寡母和寄居者的責任,這一點在美索不達米亞諸法典中並不明顯。美索不達米亞諸法典中屬靈和道德原則的缺失,和摩西法典形成了對比;在後者中,這些原則是基礎性的。最後,摩西律法是上帝所啓示的,作為祂自己與以色列百姓之間聖約關係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古代近東的其他法典中完全沒有這種觀念的跡象。這些主要的差異清楚表明了希伯來律法不同於美索不達諸法典,更別說對後者有巨大改良了。
走近《新約》
《出埃及記》敘述了這一片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到目前為止,這是《舊約》中最偉大的救贖事件。它本身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行為,但它的更偉大之處在於預表了耶穌基督更高的救贖工作。正如本章前面部分指出的,基督是最終的逾越節羔羊,祂流寶血拯救自己的百姓脫離死亡和黑暗。正如保羅在《歌林多前書》五章7節中所說:「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除了「救贖」這一中心思想,《出埃及記》還以其他一些方式指向了基督。例如,《出埃及記》二十五章至四十章中建造的帳幕,就是基督的預表。《約翰福音》一章14節說:「道成了肉身,設立帳幕在我們中間。」(本書作者自己的翻譯);道本身就是耶穌基督(見約一1-5;啓廿一1-3)。事實上,贖罪日當天,大祭司會進到會幕中,彈血在施恩座上,這一行為預表了基督為自己百姓的緣故流血贖罪。例如,在《羅馬書》三章24至25節,通常被譯作「挽回祭」的希伯來文單詞實際上的意思是「施恩座」。因此,這處經文的正確解讀是:「上帝藉基督耶穌的寶血設立祂為施恩座,[人]在祂裏面憑信心被接納。」(本書作者自己的翻譯)因此,不僅對會幕本身,而且對「贖罪日」這個事件,基督都是其最終的成全。
我們還能很容易想到許多其他相似之處和預表,比如摩西暗示著基督,嗎哪預表著基督,但這一信息是始終成立的:《出埃及記》中包含了許多有關將要到來的彌賽亞的影子,這些影子將要在耶穌基督的顯現、位格和工作中成為完全的現實。
在《出埃及記》十五章,以色列在上帝偉大的拯救之下過了紅海,摩西立即帶領百姓向上帝唱了一首讚美的詩歌。這是一首頌歌。這首歌開頭的一句突出了《出埃及記》的一個主要主題:「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祂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出十五1)這首歌唱完後,米利暗又帶領以色列眾婦女輪流吟唱同樣的歌詞以示回應(出十五20-31)。這些歌詞是一首更長的讚美詩歌的副歌部分,而副歌的目的是強調這首讚美詩歌最重要的教導:主耶和華得勝了,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唯有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十五章中這首詩歌的第二句強調了《出埃及記》的又一個主題。以色列百姓唱道:「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主耶和華是祂百姓的拯救者和救贖主。祂曾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雖然要在別人的地為奴,但過了四百年祂就要將他們從奴役中拯救出來(創十五13-14)。這就是祂在《出埃及記》中所做的:這是一位信守應許的上帝,將自己的百姓從壓迫中拯救出來。
最後,主耶和華不僅將自己的百姓從奴役中拯救出來,還堅固了和他們之間持續存在的關係。《出埃及記》十五章中摩西的歌強調了一個事實:「你憑慈愛領了你所贖的百姓;你憑能力引他們到了你的聖所。」(出十五13)這一事實體現在了所謂的「以馬內利原則」中:「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們的上帝。」(出六7)上帝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在西奈山上正式生效:上帝與希伯來人立了約。
參考文獻
Baines, John, and Jaromír Má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0.
Cassuto, Umberto.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Jerusalem: Magnes, 1967.
Childs, Brevard S. The Book of Exodus: A Critic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1974.
Currid, John D. Ancien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7.
———. Exodus. 2 vols. EP Study Commentary.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2000–2001.
Currid, John D., and David P. Barrett. Crossway ESV Bible Atla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Edelman, Diana. “The Nile in Biblical Memory.” In Thinking of Water in the Early Second Temple Period, edited by Ehud Ben Zvi and Christoph Levin, 77–102. Berlin: de Gruyter, 2014.
Enns, Peter. Exodus. NIVAC.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0.
Hoffmeier, James K. Israel in Egypt: The Evidence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Lichtheim, Miria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1980.
Motyer, J. A. The Message of Exodus: The Days of Our Pilgrimage. The Bible Speaks Toda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ropp, William H. C. Exodus 1–18: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iney, Anson F., ed. Egypt, Israel, Sinai: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Biblical Period.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1987.
Redford, Donald B.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rna, Nahum M. Exodus: The Traditional Hebrew Text with the New JPS Translation. JPS Torah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1.
———. Exploring Exodus: The Heritage of Biblical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1986.
Stuart, Douglas K. Exodus. NAC 2. Nashville: B&H, 2006.
Walton, John H.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 Survey of Parallels between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Librar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9.
註腳:
- Donald B. Redford, <從埃及學的視角看出埃及記的敘事> (An Egypt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xodus Narrative), 見 Egypt, Israel, Sinai: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Biblical Period,由 Anson F. Rainey 編輯 ,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 138 頁。
- T. Eric Peet,《埃及與舊約》(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of Liverpool, 1922),第 93 頁。
- 尤其見 John D. Currid,《古埃及與舊約》(Ancient 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7),以及 James K. Hoffmeier,《以色列在埃及:有關出埃及傳說真實性的證據》(Israel in Egypt: The Evidence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參 Currid,《古埃及與舊約》,前揭,頁 103。另見 John D. Currid, <出埃及記七章 8 至 13節中‘杖變蛇’對抗的埃及背景> (The Egyptian Setting of the ‘Serpent’ Confrontation in Exodus 7,8–13),見 BZ, n.s., 39, no. 2 (1995), 第 203–224 頁。
- 見 James K. Hoffmeier, <出埃及記敘述中上帝的手對比法老的手> (The Arm of God versus the Arm of Pharaoh in the Exodus Narratives), 見 Bib 67, no. 3 (1986), 第 378–387 頁; 以及 David R. Seely, <出埃及傳說中上帝之手的意象> (The Image of the Hand of God in the Exodus Traditions),見 1990 年密歇根大學博士論文。
- Umberto Cassuto,《出埃及記評註》(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Jerusalem: Magnes, 1967),第 117 頁。
- 見 Thomas O. Lambdin, <舊約中的埃及外來語> (Egyptian Loan Words in the Old Testament),見 JAOS 73, no. 3 (1953), 第 145–155 頁;Lambdin,《古閃米特語言中的外來語和抄本》(Loan Words and Transcriptions in the Ancient Semitic Languages, 博士論文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2); 以及 Ronald J. Williams, < 埃及與以色列 > (“Egypt and Israel),見 The Legacy of Egypt, ed. J. R. Harri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 Gary A. Rendsburg, <摩西五經中的埃及太陽神“拉”> ( The Egyptian Sun-God Ra in the Pentateuch),見 Henoch 10, no. 1 (1988), 第 3–15 頁。
- 與整個托拉的寫作相關的一些問題是很複雜的。例如,見Duane A. Garrett,《再思創世記:摩西五經頭一卷的來源和作者》(Rethinking Genesis: The Sources and Authorship of the First Book of the Pentateuch,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1); Isaac M. Kikiwad 和 Arthur Quinn,《亞伯拉罕以先: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統一性》(Before Abraham Was: The Unity of Genesis 1–11, Nashville: Abingdon, 1985);Gordon J. Wenham,《創世記一至十五章》(Genesis 1–15, WBC 1, Waco, TX: Word, 1987);以及 R. N. Whybray,《摩西五經的形成:一種方法論的研究》(The Making of the Pentateuch: A Methodological Study, JSOTSup 53, Sheffeld: JSOT Press, 1987)。
- Douglas K. Stuart,《出埃及記》(Exodus, NAC 2, Nashville: B&H, 2006),第 20 頁。
- 這個表格出自 John D. Currid,《出埃及記》第一卷(Exodus, vol. 1, Exodus 1–18, EP Study Commentary,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2000),第 23 頁。
- 見 Dale C. Allison,《新的摩西:馬太的一個預表》(The New Moses: A Matthean Typ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Wayne S. Baxter, <馬太福音中的摩西意象> (Mosaic Imagery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見 TJ 20, no. 1 (1999), 第 69–83 頁;John Dominic Crossan,<從摩西到耶穌> (From Moses to Jesus: Parallel Themes), 見 BRev 2, no. 2 (1986), 第 18–27頁;以及 Barnabas Lindars, <對觀福音書中的摩西意象> (The Image of Moses in the Synoptic Gospels), 見 Theology 58 (1955), 第 78–83 頁。
- 參 Currid,《出埃及記》,前揭,1:253。
- “情節主題”這個術語出自 Thomas L. Thompson 和 Dorothy Irvin, <有關約瑟和摩西的敘事> (The Joseph and Moses Narratives),見 Israelite and Judaean History, 由 John H. Hayes 和 J. Maxwell Miller 編輯,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7, 第 183 頁。二位學者將這個術語定義為“推動故事進一步發展的情節要素”。
- John D. Currid,《與神的反對:舊約的爭論神學》(Against the Gods: The Polem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 Wheaton, IL: Crossway, 2013),第 75 頁。
- 探討這種關聯的著作有很多。例如,Brevard S. Childs, <西的出生 > (The Birth of Moses),見 JBL 84, no. 2 (1965), 第 109–122 頁;以及 Benjamin R. Foster, <阿卡德薩爾貢的出生傳說> (The Birth Legend of Sargon of Akkad),見 COS, 1:461
- Gary A. Rendsburg, <與法老等同的摩西> (Moses as Equal to Pharaoh),見 Text, Artifact, and Image: Revealing Ancient Israelite Religion, 由 Gary M. Beckman 和 Theodore J. Lewis 編輯 , BJS 346, Providence, RI: Brown Judaic Studies, 2006, 第 201–219 頁。
- Donald B. Redford, <‘被暴露的嬰孩’的文學主題> (The Literary Motif of the Exposed Child),見 Numen 14, no. 3 (1967), 第 209–228 頁。
- Daniel S. Richter, <普魯塔克論伊希斯與奧西里斯的故事:文本、異教崇拜、以及文化挪用> (Plutarch on Isis and Osiris: Text, Cult, an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見 TAPA 131 (2001), 第 191–216 頁。普魯塔克的論述是相當後期的,出現在約主前一世紀,但它或許反映了早得多的文獻資料。
- 節選自 John D. Currid,《與神的反對:舊約的爭論神學》,前揭,頁 81-82。
- 參 Gary A. Rendsburg, <與法老等同的摩西>,前揭,頁 207。
- 見 Aylward Manley Blackman,《國王胡夫和術士們的故事》(The Story of King Kheops and the Magicians, Reading, UK: J. V. Books, 1988); 以及 Miriam Lichtheim 編輯並翻譯的《古王國和中王國時期,古埃及文學第一卷》(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s, vol. 1 of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第 215–222 頁。
- 例如, 見 Charles F. Aling,《埃及與聖經歷史:從最早期到主前 1000 年》(Egypt and Bible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000 B.C., Baker Studies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1),第 103–110 頁;John James Davis,《摩西與埃及諸神:出埃及記研究》第二版(Moses and the Gods of Egypt: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xodus,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6),第 98–153 頁;George A. F. Knight,《作為敘事的神學:出埃及記評註》(Theology as Narr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6),第 62–79 頁;以及Nahum M. Sarna,《出埃及記初探:聖經中以色列的遺產》(Exploring Exodus: The Heritage of Biblical Israel , New York: Schocken, 1986),第 78–80 頁。
- 例如,見 , <對尼羅河的讚歌> (The Hymn to the Nile),見 Adolf Erma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Poems, Narratives, and Manuals of Instruction, from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由 Aylward M. Blackman 翻譯 , New York: Dutton, 1927, 第 146–149 頁。
- 例如,Pritchard,ANET,前揭,頁 365。
- Meredith G. Kline,《聖靈的意象》(Images of the Spiri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0),第 13–42 頁。
- Warren Austin Gage,《創世紀的福音:對創世論和末世論的研究》(The Gospel of Genesis: Studies in Protology and Eschatology, Winona Lake, IN: Carpenter, 1984),第 20–21 頁。
- 這方面的開創性研究可見 Ziony Zevit, <對十災的三種看待方式> (Three Ways to Look at the Ten Plagues),見 BRev 6, no. 3 (1990), 第 16–23 頁,第 42、44 頁。
- 此表格節選自 Currid,《古埃及與舊約》,前揭,頁 115。
- 關於這個樣板的深入研究, 見 David Daube,《聖經中的出埃及模式》(The Exodus Pattern in the Bible, All Souls Studies 2,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第 73–82 頁。
- John A. Wilson,《埃及的主旨:解讀古埃及文化》(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第 48 頁。
- Cyril Aldred,《埃及人》, 見《古代民族和地域》(The Egyptians,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18,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1),第 161 頁。
- 參 Currid,《古埃及與舊約》,前揭,頁 119。
- John H. Sailhamer,《作為敘事的摩西五經:聖經 – 神學評註》,見《解經文庫》(The Pentateuch as Narrative: A Biblical-Theological Commentary, Libr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2),第 252 頁。
- 關於這三個詞的深入研究,見 G. K. Beale, <對出埃及記四至十四章以及羅馬書九章中法老心剛硬的解經和神學思考>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Hardening of Pharaoh’s Heart in Exodus 4–14 and Romans 9),見 TJ, n.s., 5, no. 2 (1984), 第 129–154 頁。
- 參 Pritchard,ANET,前揭,頁 54。
- 關於這種論證的更多細節,見 John D. Currid, <上帝為何要使法老的心剛硬?> (Why Did God Harden Pharaoh’s Heart?),見 BRev 9, no. 6 (1993), 第 46–51 頁;Currid, <出埃及記七章 8 至 13 節中‘杖變蛇’對抗的埃及背景>,前揭,頁 18–40;參 Currid,《古埃及與舊約》,前揭,頁 96–103。
- 這份文獻的年代很晚,出現在托勒密(Ptolemaic)王朝期間,譯文可見 K. Donker van Heel 編輯和翻譯的《赫爾摩坡里斯律法指南:(P. Mattha)⸺原文與翻譯》(The Legal Manual of Hermopolis: [P. Mattha]: Text and Translation, Leiden: Papyrologisch Institut, 1990)。
- 有可能每塊石版上都有一份十誡,一份歸領主,另一份歸僕從。以色列的那一份被放在了約櫃裏(申10:5)。相關探討見 Meredith G. Kline,《大君的條約:申命記的聖約結構研究與評注》(Treaty of the Great King: The Covenant Structure of Deuteronomy: Studies and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63)。
- Menahem Haran,《古以色列的聖殿和聖殿服侍:對聖經中異教崇拜現象和祭司群體之歷史背景的探究》(Temples and Temple-Service in Ancient Israel: An Inquiry into Biblical Cult Phenomena and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Priestly School ,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5),第 195–196 頁。
- 參 Nahum M. Sarna,《出埃及記初探:聖經中以色列的遺產》,前揭,頁 197。
- Frank M. Cross, <帳幕:從考古學和歷史學進路出發的研究> (The Tabernacle: A Study from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見 BA 10, no. 3 (1947), 第 45–68 頁。
- 參 Nahum M. Sarna,《出埃及記初探:聖經中以色列的遺產》,前揭,頁 196–200。
- 參 Pritchard,ANET,前揭,頁 159–163。
- John D. Currid 和 David P. Barrett,《十架路 ESV 聖經地圖》(Crossway ESV Bible Atla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第 67 頁。
One thought on “舊約聖經神學導論:出埃及記(John D. Currid)”